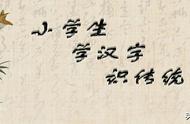鸡年第一天,有一项应景的新技能需要get,那就是在门上贴鸡的画儿。
“贴画鸡户上”,这是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的一项古老习俗,目的是驱邪纳吉,让“百鬼畏之”。至于贴门神、贴春联之类,远没有贴画鸡来得历史悠久,而且“鸡”作为一个守护神的地位其实要高于那些人格化的门神。《荆楚岁时记》就引用《括地图》说了此事:“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之。”——敢情民间熟悉的门神郁垒之类,还是金鸡大神的部下呢!
《荆楚岁时记》引董勋《问礼俗》的另一段话也佐证了“鸡”之重要性。正月初一到初七,是所谓“说畜日”加“人日”,其中“鸡”首当其冲,成为了正月初一的冠名之畜。然后才是“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这些日子的习俗和禁忌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今一日不*鸡......七日不行刑,亦此义也”。
为什么“鸡”在民俗中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需从它的诸多象征意义说起。

正旦画鸡于门。
象征光明与生命的鸡
“六畜 人”的故事,常常是和创世神话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有说女娲创世,第一日造了鸡,然后是狗猪羊牛马,直到第七天造了人。它的格局,看起来很像基督教的上帝创世,都是七天,都在创造万物的最后创造了人类。而鸡,可以作为本土“创世纪”的首物,自然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具有跟“创世”不可分割的象征意义:从混沌到有序,从黑暗到光明,鸡是其中的媒介。
我们总是辩不清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过古人给出的答案似乎是:先有蛋。在上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天地一片混沌的时候“状如鸡子(鸡蛋)”,然后这个“宇宙蛋”再卵生出开天地的神——盘古。对于盘古的面貌,正统的记载中都是人格化的,称其为一个巨人。不过民俗学家亦发现,在浙江一些地区的民间叙事中,盘古长着鸡头人身,还有一对翅膀。既然盘古都可以是鸡鸟之神,那么鸡作为创世首物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吧!
远古初民的这种鸡信仰,其实很好理解。“雄鸡一唱天下白”,鸡面向东方,呼唤日出,初民将鸡鸣和日出视为一种因果关系,于是鸡便被奉为了神物。它在中国文化中称为“阳鸟”,所以它驱散黑暗,象征光明的复生;它孕育世界,象征生命的到来。它代表着太阳,或者太阳本身就是它变的:比如《帝京岁时纪胜》等书中记载的用来祭日的“太阳鸡糕”,比如人们说的“日有金乌,月有玉兔”。
沟通人神的鸡

鸡,若非表现为动物形象的神,便也可以是献给神的礼物,作用于人与神的沟通。
以鸡作为祭祀牺牲早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云:“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 此处“鸡人”司报晓之职,以及负责为祭祖、禳祝和衅礼提供鸡牲。
不过相比于整只鸡,似乎鸡血才是那更具神秘力量的部分。所谓“衅礼”,就是以血涂抹器物来祭祀。在不少地方,“开光”仪式中也需要用到鸡血,用公鸡血在神祗或者神祗的物具上象征性地指指画画,使它们获得神的灵力,鸡血便是那个从“非神”到“神”的媒介。
鸡血也用于盟誓之中。人类学名著《金枝》中说:“一切盟誓中最有力的盟誓莫过于共食一种神圣的物质。因为这样一来,参与盟誓者如果背盟弃信,就决不能逃脱吃进腹内长在身上的神的惩罚。”结盟时饮鸡血酒,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过度亢奋,喜欢说“打了鸡血一般”,这种说法来自曾经风靡过的、所谓可以延年益寿治愈百病的“鸡血疗法”。鸡血疗法并不科学,但从其背后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原始的血液崇拜,尤其是对鸡血神秘力量的崇拜。
代表生殖力的鸡
鸡的其他属性,几乎都从前述那些属于它的神秘力量而来。
因为鸡是“阳鸟”,所以它是阳性的象征,尤其是雄性和生殖力的象征,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这倒并非中国文化的孤立现象,汉语中“鸡”可用以指代男性生殖器,而英语中的“cock”亦如此。这也是在翻译“鸡年”这类表述的时候,一般摒弃“cock”而使用“rooster”这个相对中性的词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