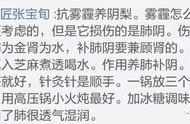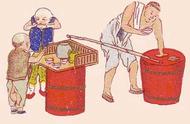河另一侧的市场/崔斯也

长途客运站/崔斯也
“市场就在家门口,但只能干瞪眼,就是过不去。”包括山水家园在内的几个邻近小区的居民,都觉得很有必要修一座桥,否则去市中心只能从小区北门绕着走,走路得多花四十分钟,打车至少十块钱。
小区居民赵姐说,如果有桥直通对面,她每天上下班坐公交车来回只需要花两元。而现在她途中得转一趟车,耗时一小时以上。
人们在盼望中渐渐失落,期待中的桥一直未见踪影。比山水家园的回迁户更早住进抚西河北侧的人们说,建桥的事情听说好久了,但从来没有动工的迹象。
无奈的居民们只好各显神通。河道上有一座东西向的小型水坝,有人在水坝两端墙面上各挂上一个轮胎,从河边栏杆翻下去,踩着轮胎,跳上水坝,从水坝上的钢板过河。但墙面很高,遇上雨雪天气轮胎变滑,而水坝上的铁板是可活动的,处处危险。还有人试图在窄河道上垫石头,但经常因行走不稳跌入水里,有老人曾因此在河道中摔成骨折。

水坝上的轮胎/崔斯也
刘富一家住在16楼,窗户正对着河道的方向,用刘富妻子的话说:“我们每天都能瞅着人掉河里,有的爬都爬不起来,像看电影似的。”
自2016年开始,刘富都在琢磨着搭一个能过河的东西。那时他退休多年,每天有大量空闲时间。雨季过后,他选定一处较窄的河道,河道下面有一条宽阔的污水管。他打算在水管附近堆放沙袋和石头,搭成桥墩。
刘富每天带着一双胶皮靴,站在半米多深的水里挖沙子,找石头。靴子常常灌水,几百斤的石头挖不出来,刘富用镐头一点点砸出来,从水里慢慢滚着石头,一趟趟搬过去。
桥慢慢有了雏形。后来几年内,这个雏形历经多次冲毁,但沙子混着水泥,桥墩越搭越高,也更加牢固。现在这座桥有钢丝固定的防水栏杆,还有钢板制成的桥面。栏杆上拴着一块红布,旁边还放着一把扫帚,很是整洁。越来越多的人从这座桥通往对岸,送外卖的摩托车也从这儿来往。

现在的小铁桥/崔斯也
只干“外面的活儿”
刘富老家在黑龙江,十来岁时最大的梦想是当兵,但因为要照顾家中的五个弟弟妹妹,他等到20岁才分配到一个入伍名额。
1973年,他进入辽宁抚顺一个武警部队,一去六年。退伍后,他没有被分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只能回到老家种地。一年后,战友老刘给他写信:“还在家待着呢?回抚顺吧,我给你介绍工作。”收到信的第二天,刘富迅速收拾东西,住进了老刘家,在当地水利局渔场做临时工。
1982年,刘富与单位同事介绍的对象结婚,在抚顺安了家。过几年他去做建筑工作,有一次往起重机的钩子上挂东西,指挥员没看好,钩子一起,把他的手一起吊上去了,手被扯到露出了骨头。开起重机的,正好是他的妻子。
那次以后,刘富在家养了几个月,再没去上过班。往后的日子,他去劳务市场做瓦工活儿,隔几天能接上一个活干,每个月挣两三千元。但一起干活的工友总是互相请吃饭,加上抽烟喝酒,月底总剩不下几个钱。
刘富不会做家务,“连下个面条都不会,在家就看看手机,看看电视,啥活也不干,净干‘外面活儿’。”刘富的妻子说。
刘富在外面干活确实很积极,过去谁家的门打不开,谁家玻璃坏了,都拜托他来修。搬到山水家园后,修桥是刘富这几年最用心的“外面活儿”。
从2018年开始,刘富决心把桥修得更好一点,天一亮就出门,带着工具到河边挖石头,所有石头用锤子砸掉棱角修整好,一个个码在一起;河道里的树枝、垃圾都一一捡出来。
桥墩上面铺一些木板,好的木板都是各处捡来的,为了运送木板还弄坏了他两辆买菜推车。中午妻子会到河边给他送饭和水,一直忙到天黑才回家吃饭。
有一次搬石头,刘富脚踩在污水管的青苔上,一头栽到河里,手机也摔坏了。回家后他没敢跟妻子说,洗澡前脱衣服时,妻子才看见他后背上有一道很大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