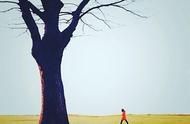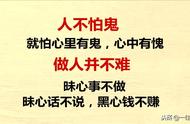(电视剧《人世间》海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俞敏洪:《人世间》里的母亲是不识字的,你的母亲识字吗?
梁晓声:《人世间》里的周家绝对没有照搬我的家庭,里面除了父亲这个形象有我父亲的影子之外,其他的儿女身上都是我对于好青年理想样子的一种寄托。进一步说,秉昆对哥们的友爱、秉义对清官的执着,包括周蓉保持独立的个性,这可能都是我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达成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就把这些寄托在了人物身上。
我写过《母亲》的小说,还写过N多散文,所以在写《人世间》里母亲的时候,我并没有着意写这个人物,《人间世》中最苍白、最不立体化、塑造最不成功的人物,其实就是周母。但我要感谢萨日娜,也要感激改编者和导演,因为萨日娜的表演使原著中比较苍白、不立体的人物鲜活起来了。我第一次看到萨日娜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但她确实身形太丰满,我想象中那个年代的母亲应该消瘦一些,但当萨日娜在镜头前出现超过五秒之后,我立刻就认定了这就是母亲,这个演员身上的那种母性魅力,甚至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每句台词。你会发现她说台词的时候,对气声的控制相当准确,她的台词能带出内心微情感的变化,这些都是演员很棒的方面。
俞敏洪:把一个艰难生活中的慈母形象演绎得尽善尽美。
梁晓声:对,所以在性情上,萨日娜非常像我母亲。我的父亲和母亲给了我不同的基因,比如同样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的父亲这样过来之后,至少在他退休之前,50岁左右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什么样的苦我都吃过了,走南闯北二十几年,独自在外挣钱养家糊口,因此他对别人正在经历的一些艰难困苦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包括对自己的儿女们,他会认为那有什么呢?他觉得我都经历过了,人是可以克服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我母亲就不一样了,她也经历了这些艰难困苦,但她就会感同身受,她再看到别人在不容易状态下生活的时候,她会心疼,所以我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更像我的母亲,这可能是一种基因。
俞敏洪:你身上有非常强大的、基于本性的善良基因,无论是你在书中对小人物的同情,还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对不公现象的愤怒,亦或者是你为普通老百姓的发声,都可以说是把善良体现得淋漓尽致。
梁晓声:主要还是因为我母亲,基因真的太奇特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家虽然在城市,但家里面有一小块空地,那时候城市允许养猪,我们家就真养了一头猪,从小养到大。但猪也是要卖的,那时候买猪的人会拿一个很长的竿子,前面有很尖锐的钩子,他们会一钩子钩住猪的下巴,直接从栏子里拖出来拖到车上,猪很害怕、很惊恐,然后就叫。我母亲那时候在家里一直哭,她相当长时间不吃猪肉。这种基因在我身上是一种什么体现呢?我那个小区在改造的时候有很多民工,天很热的时候,他们中午就在树荫底下垫一个纸板壳坐着,吃盒饭也吃最简单的。我从楼里出来看到他们,心里会有一种忧伤,这种忧伤会让我想到,他们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是谁家的父亲?谁家的兄长?肯定是那个家庭需要他出来挣这个钱,而这个钱估计一天也就二三百元。但其实有时候我不太愿意自己身上这种基因过于鲜明,因为这会使我经常处于多愁善感的状态,在生活中我看到这个事也多愁善感,看到那个事也多愁善感,所以我很希望自己要么看到的少一点,要么看到之后转眼过去,但有时候它就是过不去。

俞敏洪:恰恰是因为你身上的这种善良,才让你在写小说的时候能够把一个个底层老百姓的善良写得那么的淋漓尽致。
梁晓声:可能我更了解他们,我就成长在光字片,下乡之前都是在那样的氛围里度过每年的365天,我和大院里的孩子们、家长们都非常熟悉。还有一点相当重要,也是许多我的同代过来人说的那样,那年代虽然贫穷,但治安反而更好一些,因为谁家都没什么可偷的。我记得我们家曾经被邻居家一个长我几岁的女孩子偷去了5元钱,那时候5元钱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即使是我母亲这种会包容很多事情的人,也是一定要去报案的,派出所一定要来解决这件事。但除了这样的小事之外,一般来说邻里关系、大院关系都相对比较和谐,这种和谐给了我一种底层人家的暖意,而这种暖意,我越往后成长为青年、中年的时候,也就越觉得庆幸和感恩,如果生活已然那样不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再雪上加霜,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俞敏洪:为什么往往在底层艰苦条件下生存甚至是挣扎的人,反而在更多的时候体现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为什么明明在往上走的人,经济条件好了,有社会地位了,自私的一面或者势利的一面却体现的更多?当然往上走的人里也有好人,比如你现在算是中国的知名人物,物质、地位都解决了,但你依然在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为他们呼吁和呐喊。
梁晓声:其实在猴群、大猩猩群体,甚至在狮群、狼群,在一切较大型的动物群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当这个群体中有一个成员要往上走的时候,终点可能就是挑战首领。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表现出相当强悍的一面,一定会有对其他成员六亲不认的一面,就算是一个新的年轻猴子或者猩猩要挑战首领,也是大打出手的。但你会发现,其他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没有能力有这种想法的群体,它们认知到它们不必那样做,所以它们相对不会那样做,原来是怎样,后来就还是怎样。
东北的情况和江苏的情况不太一样,东北人更多的是闯关东来的,不只是山东人,还有河北人,还有少数山西人,这种闯到关东来的底层人民如果不抱团取暖,最初的时候都很难单靠个人的努力去维持生活、家庭,所以抱团取暖成为了一种本能。在这个本能中,如果一个人被别人指着后脊梁说他不可交,他不讲道理,他不仁义,而这个人在底层又上升不了,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在人格上被逐出的感觉,所以底层大多数人都很在意,都很本能的要体现出这一点。
俞敏洪:所以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中,更容易出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状态。后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期,慢慢开放了各种各样的竞争,到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充分竞争的社会,考大学要竞争、工作岗位要竞争、做生意要竞争,甚至朋友之间为了友情、爱情还要竞争,很多人也因此失去了善良的一面。但也是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变得比原来富有了,中国也从不流动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充分竞争的流动社会,你认为这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合算的改变吗?
梁晓声:可以肯定的说,必须而且合算。我觉得在底层、在民间,人和人之间是能够抱团取暖的,绝大多数人会尽量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别人,这一点确实应该充分肯定。但在晚清覆灭,民国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现实?中国最优秀的那批知识分子想要改变中国,他们和民众的庞大基座是脱节的,知识分子的鼓与呼即使对民众是好的,但民众对于这些优秀的儿女们依旧缺少理解,就像鲁迅笔下写的《药》和《坟》那样。因此,鲁迅的笔下才会有郑老三,才会有红眼睛阿义,他是一个狱卒,夏瑜在监狱里还在跟他讲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为了劳苦大众,这时候他就会扇夏瑜耳光,会觉得你还敢跟我说这样的话。所以,当知识分子和民众脱节,这对于一个国家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现在的确会出现你前面提到的那些状况,但我会把它看成是人类社会转型期间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美国那个时期的文学、戏剧和电影,你说的这些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卓别林就演过一个角色,取材于美国一个真实案例,一个男士冒充绅士专门骗富有的中年女士,骗钱骗婚,最后伤害了30几个人。当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也会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在从原来那样的形态转向极大程度市场化状态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这几乎是君子国的传奇,然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君子国的。
俞敏洪:那就是超级现实的理想国了。所以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应该算是正常现象?
梁晓声:现在媒体发达了,所以这些事一发生我们就都知道了。在你我小时候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但媒体不发声,我们就不知道,而且即使媒体报道了,也不是家家都订报纸,家家都有收音机。我在兵团的时候,就有黑河市公安局到我们团里破某某案子,当时带了很多破案资料,他们就住在我们团,有一天趁他们不在,我就翻阅了,其中有一个案子,讲的是一个附近的农村人家,原本很老实,就因为有人到他家投宿,穿了一双很棒的大头鞋,结果就为了占有那双大头鞋,他们把人给干掉了,之后他们看还有一支笔,其实就是一般的钢笔,但他们是文盲,也不认字,所以就揣在自己兜里了。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这里或者那里,依然可能会存在。
我中学的时候,在我美术老师办公室里看到过一幅雕塑集,其中有一幅雕塑作品的插图可能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人马”,是希腊神话中非常强悍、暴力的一种动物。但罗丹雕的这个“人马”,马的躯体是向后坐的,人的上半身努力向斜上方挣扎、扭动,手臂上升,他要与马的躯体脱离开来,他要两脚落地。其实我从里面读出了一种命题——进化,人类要进化,当然这里是指文化的进化,经过几千年的时间,一部分人类进化了,比如受到最好的文化影响的那一类人,他自己有一种愿望,他要成为最现代、最好的那类人类。还有的人,虽然双脚落地,脱离了马的躯体,但关于人马的那些习性还存在在他的基因里,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代一代也在繁衍。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到如今仍然还是人马。中国有14亿人口,有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只是依然有人马而已,而且必然有,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人马正处在进化的过程中。
俞敏洪: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同的环境、变化会使一个人有所改变。比如到了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或者互相友善的环境中,坏人有可能就变成了好人?如果把人逼到了绝境或者各种诱惑和*不受控制的环境中,好人有可能就变成了坏人?
梁晓声:我几乎更相信那一点,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种返祖现象。虽然在心性上的返祖现象也会有,但我们说的返祖现象更多是生理上的返祖现象,是带有人马的自私、凶悍、暴力以及攻击性的返祖现象,但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面对。因此,从这样一种视角看,我不会拿这些事来衡量一个社会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因为我们有14亿人。
俞敏洪:我个人有一个信念,不管你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人群是什么样的,只要你始终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尽可能做与人为善的事情,就会为你个人的生存带来好处。

俞敏洪: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明明那么艰苦,你也看到了那么多社会的阴暗面,但你却始终与人为善,你是怎样才让自己保留了这样一种善良的天性的?你觉得保留一种善良天性对人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
梁晓声:首先是基因的问题,其次也和我读的一些书有关。我读大部分书是苏俄文学和欧洲启蒙时期的文学,他们的作品中经常会塑造一些坚韧、善良的母亲形象,这些形象在他们的影视中也有所体现,所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但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其实不太能直接面临那么凶恶的人,因为贫富差距在那摆着,在那个年代那个差距就是存在。比如我们看到一幢独立的小楼,当我们知道里面住的是抗联老革命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觉得理所当然。但当我们看到另一幢苏联小楼,即使我们很清楚这幢小楼里住的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们也不能把人家的钱给占了,因为那就是分给人家的房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班里调来一个男生,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家就住在新阳路边上,有一天他穿了一双皮鞋来上学,一个中学男生,个子瘦高,形象又挺好,居然穿了一双皮鞋,我们全班同学穿的都是棉鞋或者打补丁的鞋,当时他就坐在我后面,我经常忍不住看他的鞋,觉得他穿皮鞋的那双脚是那样的帅。我在兵团的时候,还曾经到过一个兵团战友的家里,他父亲是哈尔滨卫戍司令部下面的一个师长级的首长,到他家之后,就是觉得房子真大,那是苏联的房,有红木的地板,所以我们会实际感觉到这种贫富的差距。
俞敏洪:你为什么会从小就喜欢阅读?
梁晓声:首先,我们后来搬到光字片的时候,那个大院里有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我家里除了有个哥哥,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所以每当院里需要买煤、劈柴、挑水以及粉刷墙壁的时候,我们这些男孩子就成了全院的小工。但那时候母亲很不希望我们去串门,因为别人家都是女孩子,那我们在家里干什么?就听她讲故事。我母亲非常会讲故事,能迷住我们班好多同学。我这次回哈尔滨,一个男同学就说想起来那时候他们可爱和我妈说话了,我母亲也愿意跟他们聊。
还有,小时候我总看我哥哥他们的书。我哥哥有个同学,家里开小人书铺,有段时间我母亲出去上工,哥哥天天泡在学校,就剩我和弟弟妹妹们,我哥哥就往家里借小人书,我那时候字还识不全,就根据图画想象讲给弟弟妹妹听,所以小人书就变成了能使我们在家里度过独自时光的媒介。这样看书多了之后就容易产生想象,当然,我经常想象自己的未来,一直到初二也依然保留着这种想象。我特别喜欢想象牛郎织女,因为我觉得哪怕是在一个荒僻的地方,只要有一块地,有一头老牛,有一个织女下凡,就那样粗茶淡饭的生活一辈子,就已经很幸福了。
俞敏洪:你觉得现在你的牛郎织女梦实现了吗?
梁晓声:我现在住西三旗,那是2000年的时候买的房子,那时候比较便宜,我买了门对门的两套房,原来我准备自己住一套,哥哥从医院回来住一套,当时是那样安排的,我现在依然住在那里。那是一个很廉价的老旧小区,每平米物业费只有7毛钱,但我简单装修了一下之后,心中一下就充满了幸福感。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与人们对于财富的诅咒相比起来,贫困更是万恶之源。”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看到了贫困所造成的疾病,其实这种疾病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偷盗,我个人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因为贫困都能使冉阿让那么好的人成为犯人,那就更不用说别人了。
俞敏洪:你能够坚持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再到后来喜欢语文、喜欢阅读,据说是跟你小学四年级时碰到的语文老师有关?
梁晓声:对。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大队辅导员,我至今还记得他胖胖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是农村孩子,后来考上了师范,再后来到小学做了辅导员。当时他组织了小记者协会,但必须得是少先队员才能参加,而我不是,他看了我的作文之后,就觉得即使不是少先队员也没关系。他还推荐过我的作文,我的作文还被人用小楷抄在儿童影院的大广告板上,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当时我还没想过要当作家。《人世间》中写的把书藏起来,也是我的经历,我有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书,而且都包了书皮放在小箱子里,但当时只是想珍藏起来,没想到以后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