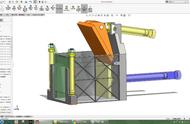广东人爱吃野味,是大多数人对岭南地区及其文化的固有印象。
历朝历代典籍和民间记录中,对广东食野的传统多有所记载。汉代《淮南子》记载,“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广东人对蛇的喜爱溢于言表;唐代《岭表录异》指出,“南中昼夜飞鸣,与鸟鹊无异,岭南人罗取生吃之”,将广东食客的食谱扩充至鹦鹉、猫头鹰等鸟类。

网络流传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一家野味店的菜单
韩愈流放潮州时,曾写下《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他在诗中列举了蒲鱼、蛤、蚝、鳖等多种野味,令其“莫不可叹惊”。作为外地人,他难以适应野味的“腥臊”,只得“开笼听其去”。
南宋周去非编写的《岭外代答》中,广东人俨然是对任何美味都来者不拒的老饕。“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大千世界,只要是能吃的,无不被用来满足广东人的口腹之欲。
有人找到1980年代公开出版的粤菜菜谱与广东美食指南,其中的食材不仅有蛇、鹤,还有水獭、松鼠、猴子与猫。光怪陆离不必多说,广东对野味的追求似乎还有向“没有最怪、只有更怪”的方向发展,比如,典型的广东名菜“龙虎斗”,在19世纪数十年间就从黄鳝煲田鸡变成蛇煲猫或蛇煲果子狸。
爱吃野味的当然不止广东人。与广东一省之隔的云南,各类花草菌蕈没少摆上餐桌。两地相似之处在于,均为古代边远地区。在耕种畜牧业尚不发达时,人们不得不寻找野味来填补物质需求。各类野生动物还能够成为家畜不足地区的蛋白质替代来源,供人们劳作所需。
但曾经的无奈之举,却逐渐变成争相追捧的风潮。有报道指出,20世纪90年代,在食蛇之风盛行的广州,每天能吃20吨以上的蛇,“吃蛇一条街上,没有吃不到的毒蛇”。这股风潮甚至影响了后来的湖南、上海和江浙,到2000年前后,上海2万家餐厅,80%都供应着包括蛇在内的野味。
有人发现,随着广东近代经济不断发展,野味开始被赋予区分阶层、彰显品味的作用。
比如,当地流传一种说法,咸竹蜂煲瘦肉或雪梨可治咽喉痛,但咸竹蜂并不见于《本草纲目》等传统医术,其疗效在清代才被“发明”出来。而后,穿山甲、娃娃鱼等野生动物被证实既难以料理,又难以食用,比起美食的享受,他们带来的更多是“身份的象征”。
广东省林业局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广州半数以上居民吃过野生动物。究其原因,45.4%的人认为可以补充“营养”,37%是出于好奇,12%则是为了显富。

对野味的喜爱,成为后来广东乃至全国的“梦魇”。
2003年,SARS从广东爆发并蔓延至全国,在全国感染超过5000名患者,并导致349例死亡。公开报道显示,SARS首例病例是2002年11月发病的一名佛山村干部,“发病前吃过蛇”。而更广为人知的首例报告病例,则是同年12月出现症状的深圳一家餐馆的野味厨师。
此前,多方研究表明,果子狸是SARS病毒中间宿主。2003年末2004年初,SARS再次在广东出现,一场果子狸“清剿”行动,对结束疫情起了关键作用。

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武林外传》截图
之前,野生动物贩卖为广东提供了大量经济收入。据报道,在SARS之前,深圳经营的野生动物餐饮场所有800余家,每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深圳销售的野生动物有近800吨,其中仅蛇类最高日消耗量就达到10吨以上。
而在广州,新源、东宝、南金、槎头四个野味市场使白云区周边成为最大的野味集散地,仅新源市场每天交易额就达190万元,年营业额7-8亿元。从野味供应方面看,广东市场在十年内增加“至少五至六倍”。其背后,是遍布广东全省的1300多家野生动物养殖场。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关停野味市场同时,当地并没有完全放弃野味销售。
2003年,当时的国家林业局等12部委发布《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上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物种,准许其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一个月后,广东上报40种陆生野生动物物种,对比此后林业局公布的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占比颇大。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人人喊打”的果子狸,也包含在内。
这为新一轮野生动物养殖埋下伏笔。2011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雷光英等人,对当时上报的鳖(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甲鱼)养殖进行统计梳理发现,广东鳖产量从2001年近2.2万吨提升到2009年3.6万吨,销售对象从珠三角地区延伸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