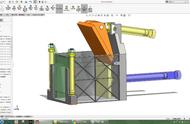图片来源:摄图网
SARS“警示效应”不过两年。据雷光英等人调查,在2004、2005两年市场低迷后,2006年初鳖的行情开始恢复。2007年底到2008年初,鳖养殖户“获得了量价双丰收”。
野味餐厅和交易市场也开始“死灰复燃”。有媒体调查发现,尽管曾风光一时的槎头野生动物市场已不复存在,但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地下交易市场。凌晨变成野生动物卖家的活动时间,趁着夜幕,大量野生动物从这里流入各个餐厅。
2007年,当地媒体写道:
“只用三四年的时间,这些人就忘了SARS肆虐时期的满街萧瑟,忘了‘全民口罩’的恐慌,忘了‘全面禁口’的谨慎,更忘了人类SARS冠状病毒动物源性的主凶就是果子狸,只剩下‘吃了保证没事,不吃反而有事’的大无畏。”
而原本未进入“白名单”的蛇,最终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得到养殖许可。2012年,广东对此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进行修编,在“经营利用管理”部分中,再无“白名单”一说,仅“禁止非法加工、食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广东也曾对禁止野生动物食用出台过相关文件。
2003年,《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要求“摒弃吃野生动物的习俗,不吃受法律法规保护、容易传播疾病或者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同年,深圳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若干规定》,明确禁止食用包括蛇在内的野生动物。
2012年,《广东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迎来修订。但与其他省份类似,“保护”变相成为“利用”,禁令反而为野生动物销售和食用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于养殖野生动物,坊间一直存在两种声音——
支持者自然为广大食客以及背后的整条利益链撑腰;
反对者则认为,在“许可证”背后,食用的野生动物难以追溯源头,其中很有可能包含大量猎捕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植物保护专家蔡宪文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技术含量要求高,但从野外直接获得野生动物却比较简单,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今年1月底开始,一场配合疫情的清剿活动在广东展开。
广东森林公安机关通报结果显示,整治市场、酒楼饭店等经营17523个次,立案74起(刑事案件14起、行政案件60起),仅收缴的野生动物就达到4390头/只。
来源不明问题还带来一条延伸至国外的产业链。据广东自然资源厅官方平台报道,近几年,广东打击多起野生动物走私案,大量穿山甲冻体、鳞片从东南亚运往广东。

广州海关截获的穿山甲鳞片 图片来源:海关发布
但反过来,禁令也让大量以养殖野生动物为生的农户面临难题。有数据显示,广东目前有龟鳖类养殖场点9万个,从业人员34万人,现行总产值近千亿元。仅中华鳖一个物种,广东一省2019年产量就达6.3万吨,带动从业人员超过1.1万人,年产值超过36亿元。
有农户烦恼,新投入的鳖苗要等几个月后才有产出,鳖的养殖环境并不适合鱼虾,禁令之后,投入的鳖苗、厂房、硬件全部都付之东流,其造成的大量损失恐怕难以承担。
对于“一刀切”的担忧,3月4日,农业农村部已发出紧急通知,乌龟、中华鳖、牛蛙不在禁食范围。
但在那之前,食客已经率先感受到禁令带来的“冰冷”。早在2月4日,在大众点评上,以“蛇”为关键字搜索,荔城、榕记这些老店名店已经杳无踪迹。
这几天,一篇名为《野味帝国》的文章热传,其中全方位展现了中国“野味”产业链,从广西云开大山里的“猎人”、在广州迷上吃野味的女白领,到用1500平方米巨型网捕鸟、用高毒农药呋喃丹毒*野鸡……堪称“触目惊心”。文章末尾,一位网友留言:
“执法束手束脚,盗猎猖獗嚣张,食客络绎不绝,太难了。希望这次禁食野生动物,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