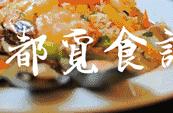而这个地方既是成都城墙内最大的「旱码头」,还是最早一批洋行建立之处,其新式早餐出现的动力与前面的通商城市是一样的。
这里再举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例子,我们知道清代的朝会与轮奏都是在每天五点左右开始,在此之前2小时左右,大小京官们都需要在乾清门外列队集合等待。
在乾清门外所谓「天街」一带,由内务府开了一片价格很贵的早点市场,而在此吃早餐的官僚都是准备面见皇上,所以在清代官僚的文集,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个早点市场的记录。
从这些记录看,在前期康熙乾隆时,内务府卖的早点还非常传统,几乎全是由水煮方式制作,普通的如粥,面,有带有北京特色的杏仁茶,炒肝,还有专门为满蒙贵族准备的酪羹,羊汤。
到了光绪后期,则主要变成了油饼,馃子,煎包,牛羊肉卷饼等,明显受到前述早点饮食近代转型的影响。
而在南方,以早茶闻名的广东,相对特殊一点。
其实江南地区也有吃早茶的习俗,不过没有广府地区如此兴盛。
乾隆时期一口通商,让广州成了中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商业、经济都很繁荣,哪怕是平头百姓也喝得起茶。
对于贸易兴盛的广东人来说,必须有一个地方在早上供人们谈生意和交换信息,茶楼就恰好提供了这一场所。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茶点相反越来越丰富,盖过了茶水的重要性。

我在上一期内容中提到星巴克第三空间的概念,其实早在广州就存在了,茶楼就是我们的第三空间。
我强烈建议早茶店连锁开遍全国,并且24小时营业,那还要什么星巴克?
我能带着电脑在茶楼吃,哦不,肝视频一整天!
03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现代的早餐,基本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
他们早早起床,就要参与到工作中,尤其是码头工人,对体力的要求极高,因此早餐就格外重要。
所以,廉价且易于获得的碳水,很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早餐。
而我们的劳动人民也是颇具智慧,哪怕是简单的碳水,也硬生生玩出了各种花样。
我们必须意识到,美食的概念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许多早餐,一开始就是穷人的食物。
但是随着阶级被打破,曾经所谓的贵族也要和老百姓一起蹲在马路牙子吃热干面,在寒风中买上一个煎饼果子,或是来一碗动物的下水。
营养这件事情,是相对的。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许多食物可能都不算优质。
但是在那个吃都吃不饱,还要做重体力活的年代,提供能量的早餐,简直就是保命。
哪像现代人坐办公室的,稍微起晚点,干脆把早餐和中餐合并,一下从三餐制,恢复到两餐制了。
Brunch甚至成为中产的代表性饮食。
要知道,现在咱们称之为垃圾食品的炸鸡、薯条,那扔到古代,都是救命的东西。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白米饭是垃圾主食,一无所长。
但在我小时候,我妈都会常常跟我讲,他们那时肚子里没有油水,人都特别能吃米,哪怕一个姑娘拍下两大碗米饭也不在话下。
脱离实际情况来评价某些食物就是垃圾,是片面的。怪就怪我们发展太快了,短短十多年就从吃不饱到要节食。
张教授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更不是什么崇洋媚外。尤其在特殊时期,更应该遵循科学的方式吃早餐。
我过去就一直说,我们国家其实还没富到那份上,我们人均摄入动物蛋白还不够,最好是能家家户户每天都吃得上牛肉才好。
不过我觉得恰也不必与人争论白米饭和白粥到底是不是优良主食,尤其是和长辈。

几年前我了解了点所谓的营养学,好不容易回家吃一次饭,就要和他们掰扯主食的问题、营养的问题。
最后,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当然也说服不了我。
直到我有一天突然觉得,我强迫他们接受我观点的样子,像极了小时候,他们强迫我接受他们观点的样子。
坦白讲,那只是一碗白米饭,只是一碗白米粥罢了。
张教授让你多吃三明治和牛奶,不要吃粥,不是要你一辈子不要碰白粥,看到白粥就倒掉,除了三明治和牛奶,什么早餐都不碰。
为了这些事情争论,最后无关科学,不管是我们的爸妈还是张教授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好罢了。
在我看来,早餐,是一座城市最基础的饮食文化,是它开启了整个城市新的一天。
在武汉,这是一份热干面。
在上海,这是一份小笼包。
在南京,这是一碗鸭血粉丝汤。
在河南,这是一碗胡辣汤。
在天津,这是一份煎饼果子。
在昆明,这是一碗小锅米线
这些都是深刻在记忆中的味道,就像我每次回家都必须去小时候常去的早餐店买一份豆皮一样。
即使我们的早餐都是碳水组成的,也没必要妖魔化碳水,谈早餐色变。
吃你想吃的,毕竟都996了,心情愉悦有时候比营养更重要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