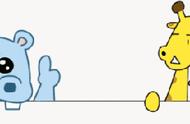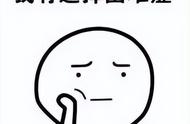严复的《天演论》翻译自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但书中的主旨更倾向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的观点。
斯宾塞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创建了“天人会通论”的理论体系,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但他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也运用于人类社会。对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不同意,主张要用伦理学来调整之,以“伦理进程”的“以人持天”,即人治力量来制约“宇宙进程”的自然力量。也就是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所指出的严复的“天演”一词概念,为“天行”和“人治”两种力量的调整、谐和。
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势衰微、列强凌逼,严复出于“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强烈现实需求,偏向于斯宾塞的“宇宙进程”的自然力说,但客观上因其著作卷帙浩大,字数偏多,翻译不易,所以他选用了赫胥黎的简明文本,但在翻译中添加了不少自己的悟解,特别是他的“按语”,让人甚至感到他只是在借赫胥黎这只酒杯,来斟斯宾塞及严复自己的酒。
斯宾塞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恒久不息的力,这种力体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自星云凝聚为星体始,地球上的生命体(包括人这一族类)出现,世间万物就无时无刻不在彼此竞争、相互绞*,“物竞天择”这一宇宙“进化之力”不可能停息。竞争之后,再经自然与社会的选择,优胜劣汰,优者适合于环境,便繁衍壮大;劣者因不合于环境,就淘汰消亡。
严复也肯定宇宙中这种永恒之力,在《天演论·序》论及“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乾坤为“质力相推”而构成。严复以“力”解“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之力,永不止息,人应效法之,自强奋起,永远行进。
严复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物竞天择”的道理。例如,澳洲本土的蜂没有针刺,但后来移民者带来有针刺的蜂入境,无针的土蜂没几年就灭亡殆尽;有一种植物叫番百合,原长于地中海东岸,后移植到南美洲,蔓生数十百里,一眼望去,其他草木都不见了。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强者把生活资源都占据了,所以“丰者近昌,啬者邻灭”。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迎合了晚清爱国者们救亡图存的心理需求,转化成为强大的社会性推动力量,严复成了“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天演论》也由此风行全国,几近经典之地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时成了国人的口头禅,连中学老师都要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写“物竞天择”的作文。曹聚仁曾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像胡适,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来自“适者生存”;像陈炯明,取名“陈竞存”,也是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
1899年,19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上学,他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的知识:“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由此,鲁迅开始了对赫胥黎、斯宾塞、严复等人有关进化论思想的接纳与扬弃,开始建构初步的学理体系。
但对《天演论》的思想功能也必须一分为二。“宇宙过程”所操纵的人类天性,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行”法则,若否定它,人这一族类或国族将遭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压迫而毁灭;但若对此“天性”放任自流,崇奉丛林法则,从而放弃“伦理进程”,放弃“人治”,我们也将遭到发自内部力量的颠覆而毁灭。
必须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一点上鲁迅比严复来得清醒。1908年,他在《破恶声论》中斥责兽性的丛林法则缺失了人的伦理本性,这种兽性、侵略性的思想苗头若不加以制止的话,定会把国人与民族引向歧途。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