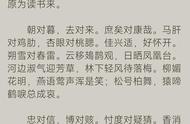1951年,蔡迺群(右一)和哥哥蔡迺绳在枕流花园
访问员:以前的花园是这样的吗?
蔡迺群:以前这个地方花草没这么多,看上去很干净。这里面有两个三角形的小地块,我印象很深的。关键是这里的一个水池很漂亮,(中间)有个喷泉,里面养了鱼,我们不太敢下去。有一个传闻失实的地方就是介绍枕流公寓的时候就讲公寓底下有游泳池,那是没有的,是有点徒有虚名了。大楼里面有专门开电梯的,很规矩的。电梯工编成1号、2号、3号、4号,轮流开。还有水电工、司炉工都是他们(物业配备)的。我们刚进来是有热水汀的,后来就没有了。家里可以享受热水汀嘛,暖和一点。
访问员:你们后来从复式搬下来之后住在哪一户呀?
蔡迺群:我们搬到五楼之后住的这一套,是整个枕流公寓里独立面积最大的。因为住房宽敞,离小学又近,所以学习小组就安排在我们家。后来小学同学聚会时,他们很多人都回忆起来:哎呀,我们在你家里怎么怎么样。我自己印象倒不是很深,他们都记得很牢。
访问员:您小学是在哪里读的?
蔡迺群:就在这里旁边。
访问员:改进小学?
蔡迺群:原来叫改进私立小学,是私立的。后来哪一年改成了华山路第二小学,我记不得了。
访问员:小学时候学习小组是几个人呢?
蔡迺群:大概七、八个,好像男同学女同学都有。
访问员:都在一起干点什么呀?
蔡迺群:就学习呀,比如说老师安排的东西,做作业啊,做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花园嘛,可以玩耍。以前没这么多花花草草的,还可以踢球的。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班里来了两个像调干生一样的,就是部队里面的小孩,但是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要大得多。中间有一个我记得叫汤震英,我印象很深的,就在这里踢球。看到我们男孩子踢足球呢,她很喜欢,她说我来当守门员。最后,就在这个位置,我印象很深的,有个同学踢球,一下踢在她肚子上,痛得趴在地上了。我母亲比较贤惠嘛,总要弄点点心啊、水果啊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印象很深,我倒反而没什么印象。
访问员:除了踢球还玩什么?
蔡迺群:玩的东西蛮多的。我们以前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六七个小孩。这个花园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很大的。记忆犹新的就是“官兵捉强盗”。什么叫“官兵捉强盗”呢?就是分成两路人马,你一边是八个,我一边是八个。大家聚在一起,拿两块石头。这个石头在这里,有这么大,是我们的。那块石头是你们的。看好以后,大家分散。原来这里都有一小块像三角形一样的绿化,你必须把这个石头埋在这个三角地块里边。埋好以后,晚上大家派兵,就派“侦察员”过去试探,谁能够拿到对方的这块石头再跑回来,就算胜利了。如果你跑到对方阵营被他们抓住的话,那对不起了,你要手搀手,拉着那棵树等在那里。第二个被抓住的再搀手接上去。我们叫官兵捉强盗,那时候很好玩。我们都喜欢晚上在底下玩。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听大人讲故事,鬼怪故事什么的,听的时候都很喜欢。听过之后,都不敢回去了,躲在那里。当时我们二楼有个姓乐的,他家小儿子跟我哥哥是同班同学,现在在美国。他家那个大哥最喜欢吹了,一肚子的鬼故事。我们就坐在这个“鱼缸”(即小水池)旁边,大家围成一圈,他讲故事。讲到最后,大家都不敢回去:“你先走”,“他先走”。然后大的在前面走,小的跟在后面。蛮好玩的小时候。

1951年,蔡迺群(左一)和哥哥蔡迺绳在枕流花园
访问员:有没有特别要好的小伙伴?
蔡迺群:特别要好的小伙伴应该说都分开了。以前我算皮大王,很调皮的。我们打球嘛,球一下滚到隔壁去了,从外面过去捡要兜圈子啊,我们就直接翻墙过去,那边是儿童福利会。我们喜欢抓蟋蟀,也直接从墙边上爬过去。墙上面经常会出现蟒蛇蜕的皮啊。还有个(调)皮的事情,我跟你讲。我跟二楼的——他也搬走了,也是住了蛮长时间的——姓王的,比我小一岁。我们皮到什么程度呢?就跑到楼上面,去干什么呢?现在想来是非常危险的,西瓜皮吃完了,往底下丢。现在说是违法的,不可以这样搞的,小时候又不懂的。一摔,摔在人家头上了,(正好摔在)踩三轮车的(人)。那么(他就骂):底下骂了,我们就逃啊,他也不知道你是哪一楼的,找不到。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照手电筒。三节一号电池加在一起,要照什么呢?照驾驶员。以前48路公交车蛮少的。谁有本事谁敢照?晚上,48路过来了,我跟他们“啪”一下照过去,那个驾驶员一个急刹车跑出来:“小赤佬!”我们就跑啊跑,跑到里面去,他在后面追,也追不到。这个多危险啊,好在以前路上没什么行人。我们调皮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还有我们这个八楼,八楼有个水箱,八楼呢,也可以上去,但是比较危险。小时候的八楼,蛮高的了,不像现在高楼大厦这么多,以前这个地方……
访问员:枕流最高。
蔡迺群:嗯,以前华山路叫海格路,属于法租界的。静安宾馆叫海格公寓,以前就两个公寓最有名的,海格公寓跟枕流公寓。当时什么淮海大楼,那不出名的。因为这里跟李鸿章有关系。包括丁香花园什么的,跟李鸿章那个小老婆有(关系),是不是她,丁香丁香嘛,是不是(属于她的),我们搞不清楚。反正这么回事。
访问员:你刚才说八楼……
蔡迺群:八楼有个水箱嘛,有个楼梯,铁的梯子,我们爬上去,跑到上面把水箱盖拉开来。那很危险的,然后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躲在里面体会一下。你说皮不皮啊?当时就是调皮呀。还有斗蟋蟀,跟王善述,我的老朋友,我们现在还玩的。我们喜欢斗蟋蟀嘛,自己抓又抓得不好,去买。我很蠢的,巨鹿路上有一个瘸腿的师傅,专门是卖蟋蟀的。那时候是1960年代了。我那天跑去看,那个蟋蟀很大,像蟑螂那么大。他开价12块钱,不还价。那时候的12块是不得了了。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零用钱就5毛钱。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小商贩推着个车子过来,什么牛筋咯,什么甘草条咯,什么橄榄咯,1分钱就可以买两块牛筋,你想想看,5毛钱已经很实用了。当然那是1950年代的,到1960年代嘛可能就没那么实用了,但是12块钱买个蟋蟀也是(很奢侈的)。我那时候零用钱揣在那里,我在动脑筋了,压岁钱是不是能买啊?后来一狠心把它买下来了。结果这个蟋蟀买下来没人跟你斗,你这个太大了,人家蟋蟀一看,不跟你斗。所以到最后这个蟋蟀怎么死的,我都忘掉了。反正买了以后像古董一样放在那里,没人跟你斗。我们还调皮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斗蟋蟀,斗蟋蟀嘛斗出经验来了。这个蟋蟀咬了半天,最后输掉了。输掉把它摔掉,你舍不得,那么有两种办法可以使它起死回生。一种就是放在手里,往上甩,甩三下,然后再甩三下,这个蟋蟀头晕了,然后放下来,它好像自己没有输过,它又斗了,这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是什么?把它闷在水里面,它好像有点溺水了。然后放上来,放上来以后它在那里休息了半天,过了一会儿,它又翻身起来了,把前面战败的事情都忘掉了,还会再来。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经验跟汽车间一个叫周小弟的一起斗蟋蟀。他那个蟋蟀厉害,我们斗不过他。斗不过他我们就出鬼点子了,一个人在跟他斗对吧,然后一个人把输掉的那个蟋蟀再去甩,甩过一会儿再斗。(轮流)斗到最后把他斗输掉了咯,他讲:“你们两个蟋蟀本来就输给我的,怎么又把我斗输掉了?变我输掉了?”实际上是我们搞的鬼点子。所以想想小时候,好玩是蛮好玩的。
还住五楼的时候,我买了一个肥皂箱的炮仗,以前肥皂箱都是木板箱,进口的肥皂。就放在那个房间里,我印象很深的。那么我就放炮仗,嘣啊嘣啊,往底下丢。我用来点炮仗的蚊香就搁在(肥皂箱边沿)上面嘛,一下掉下去了,正好掉在一个(烟花)的导火线上面。烧起来了,一下“乒啊啪啦乒啊啪啦”,搞得房顶上面都黑了。后来从小带我的那个保姆,她说:“你搞什么东西啊?”拿了一铅桶水,一下就浇上去了,没有引起火灾。还有嘛就是我们住在这里的三楼,人家底下晒席梦思,我们在楼上放炮仗。一个炮仗掉下去了,掉在席梦思上,“呜”地烧开一个洞,把席梦思烧穿掉了。最后我们赔了他一个。我父母是不打的,他们是以教育为主。我记忆犹新的就两点。我父亲是做生意的嘛,他国外回来的,他说:做人一定要有诚信。这是我记忆犹新的。我母亲是:做人一定要与人为善。我们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的。

访问员:您跟枕流的其他邻居有交往吗?
蔡迺群:碰到嘛,大家就是老朋友。叶新民是叶以群家的长子,跟我关系最好了。我经常去叶家,因为他家有很多藏书,所以我喜欢看外国文艺小说,在他们家看了多得不得了的书。我们家里的书全部抄掉了,没有了。叶家的书没抄。有的时候,半天的时间我都在那里看文艺小说,罗曼·罗兰的、果戈里的、海明威的、杰克·伦敦的、梅里美的,很多很多,还有古汉语书。所以我很多书都在他那里看的,吸收了很多营养。
大学录取通知书
访问员:小学毕业之后,进中学是什么样子的?
蔡迺群:我是1959年(小学)毕业的,考到了复旦中学。在华山路上,48路两站路就到了。
访问员:那你那个时候上中学就要坐车去了?
蔡迺群:对,48路呀。我们那时候经历还是蛮复杂的。为什么呢?我当时是搞游泳的,参加长宁区少年游泳队。后来长宁区把所有的运动队,都集中到番禺中学。所以当时我(在复旦中学)就学了一年半,初二下学期就转到番禺中学了。
访问员:那读大学是哪一年呀?
蔡迺群:我是最后一年,就是1965年进大学的,“文革”前了。
访问员:是哪个大学啊?
蔡迺群:上海师大。为什么进上海师大呢,还有个故事。因为当时是讲贯彻阶级路线的,讲出身的。因为我们是资本家出身嘛,成分肯定不行。我的体育成绩蛮好的,参加长宁区少年游泳队,得过冠军。临近考大学了,番禺中学的体育教练周老师想推送我到上海体院运动系,可惜正好那年不招游泳队。没有游泳队,那你有什么特长啊?我个子不高,但投掷蛮好的。高二的时候,手榴弹投了63米,破了校纪录。有一次参加长宁区少年运动会,标枪决赛第二投把区少年纪录破了。其实我从来没训练过,就是爆发力好呀。因为这两个事情,体育教练就说:“你就搞田径吧,考体院。”高考前,体院要摸底,我们投掷队去了三个人,但是当天发挥很一般。我就知道危险了,就正常参加高考吧。当时高考录取率很低,大概就15%左右。因为贯彻阶级路线嘛,就更是这样了。高考过后,第一批发通知,没有。我想完蛋了,还有什么花头啊?因为我填志愿的时候,知道肯定进体院的,当时我这么以为啊,所以北大、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全都是全国一流的大学。你知道我考不进的,就瞎填。最后8月10号第一批通知,没来。第二批发通知了,我回到家里,保姆跟我说:“招生委员会打电话来,叫你去一次。”我想招生委员会跟我什么关系啊?后来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了,跑到学生处,坐在那里,也没人理我。坐了大概半小时吧,就看到各种档案在眼前来来去去。旁边一个女老师终于跟我搭话了:“哪里来的?”我说:“番禺中学的。”“叫什么名字啊?”“蔡迺群。”“哦,现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你。” 我就说:“我没填过这个志愿啊。”“你想念吗?”“我不想念。”“不想念就自动放弃。”我想好歹是个大学对吧:“我愿意。”“好”,她拿了个信纸:“自己写吧,本人愿意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下面签名,时间。”我写好了,她马上拿了个信封:“来,开你家的地址,开你自己的名字收。”实际上,这就是录取通知啊。果然第二天,东西到了。我爸爸想了:你这个皮孩子还能考进大学啊。

进了大学以后,有好多课要学,其中还有叶以群的文艺理论课和文艺批判,当时的院长是廖世承。因为我是高校游泳队的,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要出去游泳锻炼,要参加全国比赛的。后来参加校运动会,手榴弹一甩又得了前两名,校田径队把我招去了。师范学院有两个特点,第一不要交学费的,第二,吃饭不要钱。上午有稀饭、馍馍什么的,中午有一顿大荤,晚上就一顿素的,这已经很好了。我参加了运动队以后又升级了,晚上那顿也能吃荤的了。
没多久就“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北京去“串联”,看了几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东西,最后就回来了。
半个安徽老乡
访问员:后面是插队落户吗?
蔡迺群:我没有,插队落户是后面的小孩,后来就“复课闹革命”了。当时很多大学生谈自己的观点,我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彻底平反了。
访问员:后来就到了安徽了?
蔡迺群:后来把我搞到外地去了,阜阳地区底下农村中学。在这之前,到大丰农场也呆了两年多,劳动。贫下中农都说我好呀:“你看,小蔡多好呀,本来什么都不会,现在挑担挑两三百斤,插秧比农民插得还快。”割稻什么,我都学,拼了命学啊,后来我就被分到安徽去了。我们算1969年毕业的,补了一点钱,当时才能结上婚呀。我夫人很好,她一个在上海工作的,找了我一个“反革命分子”哦。
访问员:结婚的时候您还没有平反吧?
蔡迺群:没有平反。不容易吧。
访问员:您是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蔡迺群:1984年,也是因为我爱人的关系,我调回上海了,照顾夫妻关系。
访问员: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啊?能说说您跟您太太吗?
蔡迺群:太太是介绍认识的。我1970年隔离审查出来后谈恋爱的,两个人关系一直蛮好嘛。记得第一次谈朋友的时候,她还请我到国际饭店吃饭了。当时她已经工作了,跟我一届的,分在上海金属材料公司,待遇还算可以的,她也蛮孝顺家里的。自己就三四十块一个月,拿十五块钱出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所以我现在一直很感恩。而且她跟我同年同月同一天生。我到现在都没听说过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对她我永远感恩吧。
访问员: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
蔡迺群:1975年。我已经到安徽工作两年了。
访问员:结婚是在枕流公寓吗?
蔡迺群:在枕流。我太太在枕流待了30多年了。
访问员:你们结婚那天是什么情景啊?还记得吗?
蔡迺群:没什么咯,那时候也没什么条件,对吧?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嘛,就很简单的,买了个五斗橱,买了个大橱,大家七拼八凑的,就在家里面过。两家人一起聚一聚。
访问员:家里自己烧吗?
蔡迺群:家里自己烧,我爱人姐姐烧的。
访问员:亲朋好友聚一聚吗?
蔡迺群:没有亲朋好友的,就我们两家人家聚一聚。以前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像我们女儿结婚请了这么多人,不可能的了。当时能够结婚就不错了。要没有那笔补贴,还没有资格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