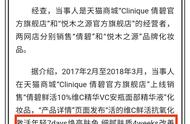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瘟疫可能要属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这场“黑死病”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它不仅带走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也带走了旧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宗教教条。
某种意义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译林出版社)是一部“黑死病”带来的文学作品。按照薄伽丘的描述,故事中的十个年轻人,正是为了躲避瘟疫而逃到了郊外,用讲故事来消磨郊外无聊的时间,这些故事的合集就是《十日谈》。
《十日谈》开篇便提到了这场可怕的瘟疫,瘟疫恐怖到“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瘟疫作为一种时刻笼罩的死亡威胁,也许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看清那些在灾难面前暴露无遗的人性的弱点与光辉。

△中世纪欧洲对抗“黑死病”的医生发明的防毒服装,包括长袍、手套和靴子,还有“鸟嘴状面具”,面具里有用芬芳草药浸过的海绵。
《十日谈》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先对十个男女集合到一起的缘由作了说明。接着,在帕姆皮内娅主持下,大家各自讲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优雅的女郎们,我相信你们天生都是富于同情心的,因此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认为这本书的开头太沉闷,太令人生厌了,令人不禁惨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可怕的瘟疫,凡是亲眼见过那场瘟疫或是耳闻其事的人,只要一回想起来,都不免会心里难受。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读着这本书叹息流泪,因此就吓得不敢再读下去了。本书的开头虽然令人害怕,可这就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这座高山之后,就来到了这赏心悦目的原野。爬山越谷越是艰苦,之后换来的欢乐就越是令人欢欣。正如通常说的,乐极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那是在1348年,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一座城市,也就是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是受了其他天体的影响呢,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加以惩罚,最初几年发生在东方,在不长的时间里,死去的人就难以计数,而且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来,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对付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打扫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建议也采用了,甚至还有些虔诚的人成群结队或者零零星星地向天主反复祈祷过了,可是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年头的初春,奇特而可怕的病症还是出现了,而且情况迅速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像在东方那样,只要病人的鼻孔一出血,就必死无疑,在这里是另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是在腹股沟或胳肢窝下突然隆肿起来,到后来越肿越大,有的像普通苹果那么大,有的像鸡蛋,一般人管这肿块叫做“疫瘤”。很快地,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位蔓延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在此之后,病症迅速变化,病人的臀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则又细又密,不过,这跟初期的毒瘤一样,都是死亡的预兆,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必死无疑。
一旦得了这种病,不管你怎样延医服药,总是毫无用处,没有一点好转的征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当时的大夫学识浅薄,总之是毫无办法,或许还因如此,除去那些医生之外,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男女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大夫一样行起医来。但是,大家都不知如何下手,因而也就拿不出任何恰当的治疗办法。侥幸治好者真是寥寥无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出现“疫瘤”后三天左右就丧了命,而且大多数都是既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

这场瘟疫很快传开来,真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传染,甚至是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病,过不了多久也会一命呜呼,而且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大路边扔着一堆破烂衣服,分明是染上这种瘟病而死的一个穷汉的遗物。这时跑过两头猪来,它们已经习以为常,便用鼻子去拱那堆东西,接着又用鼻子把衣物翻了起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了一阵。隔了不多一会儿,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又过了一会儿,它们就像吃了毒药一般,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活着的人们看到这类大大小小的惨事,不免异常害怕,自然也会生出种种怪念头来,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尽量躲开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认为,只要清心寡欲,过着节俭的生活,就可逃过这场瘟疫。于是,他们结伴来到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来,完全同外界隔绝。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好的葡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决不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也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消磨时光。
另外一些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只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笑了之,这才是对付这场瘟疫的灵丹妙药。他们果真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闯到别人家里,为所欲为。不过尽管如此,见了病人,他们却依然敬而远之,惟恐躲避不及。
浩劫当前,我们这座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荡然无存了,因为执法的官员和神父们也不能例外,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病的病了,死的死了,手底下的人也没有了,任何职务也就无从执行。因此,每个人简直都可为所欲为。
另外也有好多人采取了介乎上述两种人之间的折衷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也满足自己的*,但适可而止;他们不闭户不出,而是到外面走走,但有的手里拿着鲜花,有的拿着香草,有的拿着香料,不时放到鼻子下闻一闻,清一清神,认为这样就能消除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臭气。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便抱着一种更离经的见解。他们说,要对抗瘟疫,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走高飞。从这种观点出发,这些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切一概不管。他们抛下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自己的财产和亲人,尽量设法逃到别的地方,至少也要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
人们的见解各不相同,却并没有个个都死,也并没有个个都逃出这场浩劫。正因各有见解,各地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后来到他们自己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此一命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