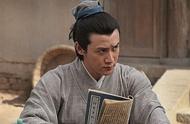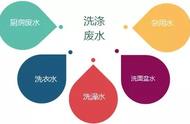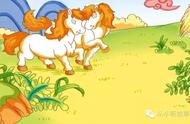文/鹤鸣甘棠
说起“唐宋八大家”,他们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他们的文风和作品一直以来为后世文人所崇拜和遵循,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其中,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生取得了文坛和政坛“双赢”的成就,更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说,他们都曾有为官遭贬的经历,比如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写下了《小石潭记》等古文名篇;欧阳修也曾因“庆历新政”流产贬职滁州,留下了《醉翁亭记》千古佳作。
此篇中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于山水之间也”,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对于欧阳修写作《醉翁亭记》的主旨,也就是他所表达的思想初衷,众多学者多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下面,我们结合欧阳修的生平经历,一一列举,并加以评析,带领大家重新审视热播剧《清平乐》里那个一样的“欧阳修”,不一样的传奇。
01“太守”之乐说读过《醉翁亭记》以后,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语言轻快明亮,节奏一如流水潺潺,再如高山仰止,读罢酣畅淋漓。
文题中的“醉翁”是谁?文中这样写到: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也就是说“太守”给自己取号为“醉翁”。
那么,“太守”又是谁?文末云: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里,我们先交待一下《醉翁亭记》的写作背景吧。
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参知政事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遭遇了朝廷反对派的重重阻力,不得不去职,远离他乡。
此时,仗义执言的欧阳修上书辩议,也难逃同谋之责,由“庙堂之高”贬到偏远之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
纵观欧阳修的仕途之路,他也是幸运的,即便被贬过,后来又风生水起,以“文忠”的谥号足慰一生,因为他生活在英明的仁宗一朝。
唐朝的柳宗元就悲惨多了,由被贬永州再到南守柳州,后来也是在北返的曙光中暗淡死去。

欧阳修在滁州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对他内心的打击是不小的。
而最可贵的是,欧阳修在蛰伏着,更在努力地履行着一位“太守”的职责。
所以,他在滁州的政绩也有目共睹的,对于“环滁皆山也”的滁州也尽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
正因此,他写《醉翁亭记》的目的呢,也是文中所写的”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可以说,一个“乐”字贯穿全文,这在众多学者心目中也是没有异议的,
这就是“太守之乐”说的缘由所在。
刘尚荣先生的《欧公居滁无乐考》中说:
文章中八次提及太守,欧公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因而这是一篇“太守之文”,此类文章不能诉苦,只能强颜欢笑。
从欧阳修一时的遭贬经历看,上述观点亦可理解,然而“强颜欢笑”岂不低估了欧阳修的“心胸”?
做大事者,谁人没有低谷的磨练。
欧阳修之所以留名史册,滁州只是他履历表中的一页促其成长的“边鼓插曲”。
此“太守之乐”说存有肤浅之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02“与民同乐”说欧阳修之所以号醉翁,是与滁州有关的,可当时他正值盛年的四十岁,自称为“翁”也是自嘲之举。
他在《醉翁亭记》中“醉”在何处?
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
这是“与民同乐”说的主张根源。
目前,这也是被大多学者认可、写进语文教科书的观点和说法。

根据程宇静博士《论<醉翁亭记>主题思想的建构、原因及影响》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支撑“与民同乐”说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 其一,从作品本身来看,“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中“乐其乐”,因“其”字的不确指使它的阐释具有了开放性,同年欧阳修创作的《丰乐亭记》中,明确指出主旨是“宣上恩德,与民共乐”,故后世读者在主题的解读上受其影响;
- 其二,从作家角度看,欧阳修为政宽简、体恤爱民的人格魅力也对“与民同乐”思想的建构有影响;
- 其三,从读者角度看,《醉记》中的“与民同乐”是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它的道德主体由君主发展到士大夫,要求为政一方的官吏士大夫也要与民同乐。
然而,这样就是确凿无疑的吗?也不尽然。
- 从其一看,程宇静的文章(以下简称程文)引用了欧阳修创作的《丰乐亭记》主旨,以此类推作为《醉翁亭记》的写作初衷。因为《丰乐亭记》的结尾这样写到: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从而,也把“宣上恩德,与民共乐”的帽子扣在了《醉翁亭记》身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丰乐亭”是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考量当地的民生现实,亲自规划建造的,也是“与民同乐”的政绩表现。
而“醉翁亭”呢,是智仙和尚建造的,《醉翁亭记》中有“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
欧阳修无非是给起了个名罢了,(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故而,“丰乐亭”之意并不等同于“醉翁亭”之意。

- 从其二看,“程文”一味地强加给欧阳修为政宽简、体恤爱民的定论,也是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实际的。
“醉翁亭”有何而来?那是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以后,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
为了方便欧阳修游玩,释放心怀,智仙特意在山中建造了一座亭子,然后欧阳修亲自起名,并为它作记,这就是《醉翁亭记》的成文由来。
据史*载,“醉翁亭”建成之后,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而且把它当作了办公场所。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
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可以说,“程文”理由的其一和其二只要站不住脚,其三之说也就不用费言辩驳、不言自明了。
因此,“与民同乐”说也是一种牵强附会。
03“乐中有忧”说众所周知,欧阳修是大文豪,不仅在北宋一朝,更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文学大家。
殊不知,欧阳修在北宋时期,他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
贯穿他一生的是忧国忧民,文学才华只是他进军仕途、施展抱负的桥梁。
即便他为支持好友范仲淹而贬谪滁州,他的初心也没有变,他也只把滁州当作了历练身心的一个过渡。
因为他知道,他还会回来的,更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他。

他刚到滁州,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客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
一个“客”字,就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胸怀。也就是说,无非是在滁州做“客”,他自信如此。
除了《醉翁亭记》,欧阳修还写了一首诗,名曰《题滁州醉翁亭》。
其中一句“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与“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是殊途同归的。
此外,他还修筑过一个亭子,与“醉翁亭”对应,取名“醒心”,叫好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记。
从中可以看出,“醉翁”之人在“醉”中,而心却是“醒”着的。作为太守,他可以“醉”,作为有大志之士,他必须“醒”。
欧阳修的滁州之旅,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受挫,人格遭侮,此时此刻此情可以说是“双面性”的,必须是愁中有乐、忧中有乐、苦中有乐的。
而“乐”呢,就是乐观,是一种积极的心态,是笑在脸上、忧在心里的处世之策。
正所谓是,“醉翁”之醉只是表象,“醒心”之醒才是关键。
虽然说,《醉翁亭记》满篇充斥着“乐”的浓厚氛围,但是呢,那“山水之乐”真正的潜台词是“忧国忧民”的“忧”。
虽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落幕了,但大宋江山的稳固久安、繁荣昌盛仍是欧阳修的心头独思。
欧阳修的一记太极迷踪拳,不知恍了世间多少文人雅士的眼睛。
年少不懂欧阳修,读懂已是半百人。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在品读《醉翁亭记》之后,深知明了欧阳修的心思,也断言文章的主旨是“忧中之乐”。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这一年,欧阳修已经六十三岁,他仍然对王安石的青苗法有所批评,始终保持着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醉翁”是欧阳修在滁州的号,后来他又以“六一居士”自称,何谓“六一”?
藏书一万,金石遗文一千,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还有一翁,在五物之间,谓之六一。
有句话说得好,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正是有了滁州或者一个个“滁州”的考验,才练就了欧阳修这样一个名垂千史的有趣的灵魂。
,平民之宴用文字点亮生活,用文化解读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