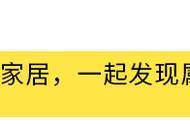初唐诗坛上,弥漫的是六朝宫体诗延续的那种“靡靡之音”,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中说得刻薄:“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眺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
宫体诗在形式上是讲究对偶、声律、用字的,内容上又不大健康,明代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说:“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在初唐诗坛上,宫体诗的生命力依然很强,恰如闻一多先生指出的那样,最先对此表示不满意的正是陈子昂。
陈子昂,就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知名的那位。
他认为诗歌应该是要有寄托、有感发的。很明显,六朝时期那种过分强调对文字的讲究,的确容易失去对内在感受的真切抒发。独具慧眼的陈子昂坚持认为,情感、心灵的自由、真实地表达才是文学最根本的价值。
而让陈子昂看到诗歌符合他预期的是魏晋时期的诗歌,他的一套理论主张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表达得十分清楚: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所谓“文章之道”结合下一句看就是“汉魏风骨”(而不是后来散文领域提到的“文以载道”的道德标杆)。下一句“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里说“汉、魏风骨”,在两晋南朝并没有被传承下来。
接下来“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这几句话是说南朝齐、梁时期的诗文字上华丽雕琢,缺乏情志的寄托,因此兴寄(“兴寄”简单来说也就是内心之兴发和情志的寄托)都断绝了。“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这几句话是说,回想古人的作品,他常常害怕风雅的理想振作不起来了。
“五百年”“晋、宋”“齐、梁间”这些时间区间梳理一下:晋、宋、齐、梁正是包含在汉、魏之后的五百年之内。
要之,陈子昂认为“汉、魏风骨”有“风雅”精神,创作表现上以“兴寄”为主,再往上追溯,汉魏诗歌这一优点是传承自《诗经》的。但是这个传统(即“道”)在汉、魏之后,即整个两晋、南北朝到初唐的这五百年之间完全被破坏了,直到陈子昂看到与他同时的东方虬才有所恢复。
因此他才会说:“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正始之音,指的是曹魏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可以和“建安”并称,可以算作“汉、魏风骨”中。

陈子昂不仅有清晰的理论主张,也有实践。《感遇》三十八首,就是他用来扭转六朝诗歌风气的一系列作品。
艺术是残酷的,注定只有原创(或者可以理解为独创、首创)作品才能被人高度肯定、写进文学史。就宫体诗创作而言,六朝诗人、乃至初唐的不少诗人,他们的作品有不少写得非常好,毕竟那种诗歌形式已经非常成熟了;而陈子昂处于草创期,写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并不成熟,但就文学史发展来看,陈子昂注定要高出一头。
韩愈的《荐士诗》中说: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韩愈批评南朝宋齐梁陈这几个朝代的诗人,作诗就好像夏天的蝉在聒噪一样,声音不动听只不过是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作文章,流于风花雪月。“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而且他们还流于辗转抄袭,没什么创意。再转一下,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一个“始”字,就突出了陈子昂的文学史地位——陈子昂是所谓的先行者、领导者。
但陈子昂是孤独的,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动摇整个诗坛,但他的主张和努力,到了后来却影响到李白。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展现诗歌理论正是对陈子昂复古理念的致敬。《古风》第一首是这么说的: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是李白用自己的理解总结了一下他之前的诗歌史,当然,是以复古为中心的。第一句中的“大雅”指的是《诗经》,尤其是其中的“雅”诗。细品一下,“雅”这个字更有一种所谓的雅正风范,它更符合李白所认为的文学正统。
《诗经》中的三个分类“风”“雅”“颂”中,“颂”一般是用来宗庙祭祀的,这可以轻易搁置一边。而“风”又是否符合李白的标准呢?
“风”一般来自民间的风谣当然,后来被采集了以后,经过了贵族阶层的整理、润色、雅化,严格上说已经不能算是民间的作品,也可视为周代贵族阶层的产物了,因此才会并称为“风雅”。但比之“根正苗红”的雅诗尤其是“大雅”(而不是“小雅”)还是差点儿意思。
李白就认为诗歌正统还是要由大雅来建立。但很可惜,在大雅之后,这个正统已经长久被忽略了,甚至萎靡不振了。李白下面接着说“吾衰竟谁陈”:可是他李白已经衰老了,还有谁能够去把这样一个衰退的正统给重新继承下来呢?
“吾衰竟谁陈”这句话相当有意思,其实李白是以孔子自比,孔子曾经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里的梦周公不是要睡大觉,而是孔子想要去继承、发扬由周公制礼作乐所形成的文化大统。孔子感慨自己已经衰老,没有精力将这样的传统给继承下去。
所以李白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就是说他要像孔子一样承担那个重大的责任一样,他李白也要承担起诗歌上的正统,甚至言下之意(“吾衰竟谁陈”)李白认为除了他自己以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有如此能力了。没错,这很李白。
接下来倒是反复申诉了:“大雅久不作”其实就等于“王风委蔓草”,等于“正声何微茫”,等于“宪章亦已沦”,反复重复着他所童心的。再往后,李白拿出了“王炸”,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固然《诗经》的正统已经沦丧,可是《诗经》之后,还存在着“建安”这个不能忽视的时期。建安诗歌恢复了正统,而建安之后诗歌又很快走上了追求绮丽的道路,而这个“绮丽”是被李白这一类的复古派诗人认为最鸡肋的,所以李白说“不足珍”。
李白进一步说:“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意思是说那些彩丽的文字遮蔽了真性情,真心灵,作为诗人应该洗掉这些,让诗歌有一个清雅、真切的面貌。“清真”二字,很容易让人想起人们习惯上用李白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概括李白诗歌语言特征。这可以说就是李白复古思想的核心、创作理念的核心。
最后“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四句话其实是在回应前面的第一联,同样是表达一种向孔子看齐的志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他的志向是,要像孔子一样删诗书,其实暗含着李白想要百年之后在诗歌史的地位,可以比肩孔子在文化史上的成就,这样,他的生命所散发的光芒就能够闪耀千年。
虽然孔子很谦虚地说“述而不作”,但是事实上,孔子修订史书,是亲力亲为的。到了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停笔,这也是《春秋》的最后一年。当他停笔之后,没有多久也就过世了。孔子之所以写不下去了,甚至失去了做事、活着的动力,是因为鲁哀公十四年发生了“获麟”的事件。
麒麟活动在野外,被眼拙无知的人给捕获,甚至还被人伤害了。得知这一消息的孔子哭了。这只本来象征福瑞的神兽,出现得不是时候,它出现在善恶混淆是非不分,人性残暴的时代,反而受到极大的伤害。
孔子周游列国,努力的要实现理想。生活的困窘,旁人乃至君王的不理解……这种坚强的意志力终于在“获麟”事件中彻底动摇了——孔子穷极一生,依旧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荒蛮。面对不了解的麒麟,人的反应是伤害它;即便不认识麒麟,也不应该去伤害。孔子所提倡的教化,终于遭受了彻底的失败。支撑孔子的意念瓦解之后,随后就是生命的终结。
李白这里用孔子的这件事想要表达什么呢?李白的意思是说,他也会为了理想奋斗终生,除了遇到类似“获麟”事件的打击。足见,李白的复古决心。

但是,总的看来,无论是陈子昂那种要与六朝文学划清界限的姿态,还是李白对建安以后的诗歌鄙夷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上看去是那么地坚决,然而实践上却并非如此。“六朝”文学中的有益养料,无一例外地被陈子昂与李白加以吸收。比如谢朓、徐陵和庾信等南朝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陈子昂与李白。
男人的话不可信,男诗人的话更不可信。【手动狗头】
我们需要明白,成功的“复古”,从来都不是完完全全地照搬;成功的“复古”,往往是另一种形式的“创新”,只不过是借鉴了“古”的优秀特质。文坛上如此,其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而在“复古”基础上的“创新”,一定是要包罗万象的。陈子昂是,李白更是。李白隔空接过陈子昂“复古”的大旗,终于走向了正轨。迎面而来的,是足以以“李白”命名的诗歌时代——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