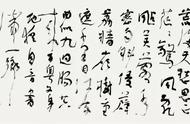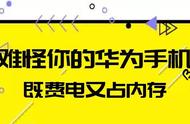《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作为柳宗元唯一一篇关于柳州山水的游记,表明他无论身处何地,对自然山水依旧怀着发自内心深处由衷地喜爱,但集数景于一文的创作手法以及成为柳州山水散文孤篇的地位,却多少让读者觉得行文匆匆,阅读审美兴致难以获得满足,同时感受到这位郊游爱好者此刻的游览远没有永州时期来得那么悠然畅快。

可以说,文章从另一个层面暗含了柳宗元柳州生活时的艰辛苦状。
首先,缠绵不去的顽疾羁绊了游历的脚步。柳宗元初贬永州,再放柳州,两处都属于南荒险恶之境。大水多雨,气候卑湿,毒虫遍野,是所谓“瘴疠”之地。因此,在永州时期,身体本就不太好的柳宗元,又增添了“行则膝颤、坐则噤痹”的关节病。
据他在《与萧翰林瀚书》中自述:“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U重浪,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靡靡,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
再贬柳州时,更可谓宿疾未愈,又添新症:“炎炎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

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寄韦珩》)在奇疮、霍疾等病痛的连续折磨下,柳宗
元大概已是形销骨立,衰弱不堪。况且柳州山水奇峭险怪,以他当时糟糕的身体状况,即使有意更多地去登临揽胜,恐怕也只能有心无力了。
其次,推行新政的操劳减少了游历的机会。柳宗元在流放地的职务身份,一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一是柳州刺史。
前者属编外之职,无实权,也不能干预政务,而且以他的戴罪之身,无诏命不得离开贬所。闲来无事,正好于当地游山玩水,在寻得心灵栖息之所的同时也成就了他散文创作的最高荣誉。而唐朝时期的刺史为州郡最高行政长官,所以柳州刺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柳州市市长,是地方父母官的角色。

可见,柳宗元被贬柳州,相较于永州时期是获得了一些对地方的实际管理权的,客观上使他早年落空的政治理想终于得到了有限施展的机会。
历史资料表明,那时的柳宗元克服重重困难,在革除当地陋俗和改善民生上做了卓绝的努力,勤勉于公务,为当地办了不少实事、好事,使得柳州的教育、法度、宗教、经济、安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
柳宗元在柳头尾约略四年,时间并不是很长,加上主导地方新政头绪复杂,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可想而知。
在此期间,柳宗元还以《雷塘祷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州复大云寺记》、《井铭》、《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柳州东亭记》等诗文记录下他在柳州进行的各项工作,可见他当时确实政务缠身并为此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

那么,他没有从前那么多的闲暇时间和功夫去对发现美景、欣赏美景,创作的山水散文也随之减少,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最后,亲朋好友的离散冲淡了游历的兴致。翻阅柳宗元永州时的山水游记可以发现,他当时并不是一个人的旅行,著名的“永州八记”里就出现了李深源、元客己、吴武陵、龚古、柳宗玄等数位亲朋。
有志同道合的好友相伴,无疑为宴游增添了获取更大快乐的因子。虽然过着苦寒的流放生活,但他们的游玩依然充满了活泼生气,“羽觞飞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颐而笑,瞪目而踞,不知日之将暮,则于向之物者可谓无负矣。”(《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及到柳州,昔日的好友如娄图男、南承嗣、李深源、吴武陵等人都已不在身旁。至亲之中,从弟柳宗直追随至柳,不久即意外身故。

从弟柳宗一也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赴荆州就职。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交替上演,让柳宗元倍添孤独愁闷之叹。
他于柳州任上涉及山水内容的诗歌,全部采用律诗绝句,寥寥数语,倾吐的多是孤身一人,无所依凭的郁结愁肠。
所以说,游山历水,固然还是柳宗元公务闲暇时愿意去尝试的审美活动,但在昔日同游伴侣多已失散的情况下,加之病痛缠身、公务繁忙,柳宗元大概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特别热衷于渲染登山临水之行,以免勾动满腹愁思,徒增心内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