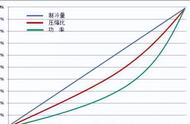假如我战死了请把我埋在那险峻的高山,
山下蜿蜒着宽敞的道路,
白云悠闲地绕过那座严关。
让我听江风呼啸,挟着民族的怒吼,
让战友们唱着凯歌回来,践踏过我的白骨。
我像高山,象高山一样庄严、雄浑。
我象大星瞪着国土,再不许敌寇侵入。
让我这无名者永远是一个哨兵,民族的歌人,
整日在山岗上了望,
看着我们年轻的后代
在欢笑中过活,在自由中生长,
脸上销尽了从前千百代的耻辱。
让日子消泯了仇恨,我依然偃息在那座高山,
山上山下开辟的是自己的土地,
集体的耕作,疏浚,安居在自己的农庄。
让我听农场上的欢歌赞扬着人类的进步,
他们瞅着埋葬我的这座高山有千年的怀古。
我像江潮,象江潮应和着他们的歌声,
我像太阳般欢笑,怡然地将他们爱抚。
让我这无名者永远是一个斗士,历史的证人,
长久在山岗上了望:
俯视着我们年轻的子孙,
管理自己的国家,建立新的社会,
脸上燃烧着是我们这一代从未有的幸福。
一九四○年五月六日,在广西武鸣旧思恩府

柳倩(1911--),原名刘智明,曾用名樊庄、凌翔等。四川荣县人。肄业于四川国立成都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从事新文艺工作。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和穆木天、杨*、蒲风、任钧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次年二月起创办《新诗歌》旬刊、月刊等。
抗战前夕,又和穆木天、杨*、任钧等出版过《国防诗歌丛书》共四册,他的短诗集便是其中之一。他因发表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长诗《震撼大地的一月间》(1934年,《综合》杂志)而知名。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工作。一九四○年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解放战争期间,为浙东解放区浙东行署文教处负责人。一九四九年底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一九五○年调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一九五三年调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和北京市戏曲研究所,长期从事戏曲改革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集《生命的微痕》(1934年,生活出版社)、《自己的歌》(1936年,乐华图书公司)、《无花的春天》(1937年,中国诗歌社)。

作为一首写于战争年代的诗歌,这首《假如我战死了》,就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风格:雄浑、粗犷、不假雕琢,直抒诗人之胸臆。
诗人开篇便假设"我战死了"-﹣带有鲜明的战争年代的气氛。"假如我死了请把我埋在那险峻的高山",诗人说,即使我战死了,也要象高山一般庄严、雄浑,以身躯筑起保卫祖国与民族的山梁,站在高处"象大星瞪着国土,再不许敌寇侵入。"战场上冲峰陷阵的勇士,就是战死了,他的锐气,他的英魂,也决不会消逝,而将永远注视着我们的民族,这是此诗给予读者的强烈感受。"让战友们唱着凯歌归来,践踏过我的白骨";"看着我们年轻的后代/在欢笑中过活,在自由中生长"。
作为一名生活在战火之中的歌手与战士,其情感豪放而坚忍,充满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他并不是在简单地讴歌战争,而是在讴歌正义、公道与自由进步的未来社会,他是要以"战死"来使未来的后代能以双手拥抱这个社会,诗人写道:让日子消泯了仇恨,在高山上偃息的我,依旧可以看到山上山下幸福的田野、农庄,那美妙的欢歌是在赞颂人类的进步。作为歌手,诗人也将参加这些人们的欢唱。他说:"我象江湖,象江潮应和着他们的歌声,/我象太阳般欢笑,怡然将他们爱抚。"这一连比喻是生动、形象和感人肺腑的,它让人们感到了流溢于诗中的一股豪气。在诗的结尾段,诗人进一步抒发了对于理想、对于未来社会的憧憬之情:作为一名当年的战士,历史的证人,诗人将在山岗上长久地了望,看子孙后代,自己建设国家、管理国家,他们的脸上将闪烁着"我们这一代从未有的幸福"。
诗作写于一九四○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华大地到处燃烧着战火,成千上万的人民和战士每天都在流血,爱国的热情与青春的诗情融为一体,表现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怀,构成了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假如我战死了》就突出表现出了这一点。在诗中,我们看不到"五四"前后诗人们奇妙瑾丽的诗境与幻象,也听不到诸多诗人在二、三十年代里的那种淡淡的忧愁与感伤,血洗国耻、振兴民族的强烈时代精神,使个人的喜怒哀怨不能不与之契合一致,在这种特定的时代精神影响下,诗歌不能不更多地具有社会功利意义。这时的诗歌一般都写得激昂、雄壮﹣﹣因为它要鼓舞着战士们奔赴战场*敌,柳倩的这首诗亦是如此。

从诗的象征性构思、从诗的诸多形象、比喻等,我们都可以发现诗人在创作时是很注意艺术性的,但作为一首写于战争岁月之中的抒情作品,一首充满英雄主义与献身精神的作品,诗人不可能过多地在诗的美学价值上作过多的思索与流连,或者毋宁说,这种英雄主义本身就构成了当时至高无上的美,而其他所谓更纯粹的美,均与这种战场上的壮美情趣颇不谐调。这似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一意义上来读《假如我战死了》,也许我们的目光会得更远一些,不但能理解本诗,而且可以窥见当代特定的审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