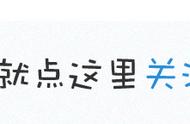《实践论》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哲学著作,它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现在我们撇开其他内容不谈,单单考察知和行的先后关系。
在《实践论》之前,中华哲学的发展已经对知行先后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
第一种是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它的补充是《尚书》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主张认识在前,实践在后,但实践比认识更重要;
第二种是王守仁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互相规定、不分先后、不分轻重;
第三种是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其理论依据是“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认识和实践可以分离,尤其以实践为当务之急。

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等人都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知,一种是“闻见之知”,需要通过感官才能产生;另一种是“德性之知”,不假于见闻,它发自人内在的本性,例如人即使不借助视觉、就算闭上眼睛也能准确的指出自己的口鼻之所在。这与数百年后培根的经验论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类似。既然知识里存在天赋的“德性之知”,那么它自然是不依赖于实践,从而就在行之先了。这是“论先后,知为先”的第一层含义。
此外,朱熹继续扩展,他不仅认识天赋的“德性之知”在行之先,而且后天的“闻见之知”也在行的前面。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如果没有确切的认识,那么就不会产生行动,行动的结果也不能达到目标,只有“真知”才有“力行”。因此,要把认识放在实践的前面。但“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所以,又要把力行提到更重要的地位。
《大学》里,“格物致知”在“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面,可是“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之所在。就如“博学于文”的目的是“约之于礼”一样,遍读圣贤书,穷尽天下之理,为的是更好的做自己并推己及人。
因此,宋儒认为认识先于实践,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读过《实践论》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片面的“真理”。

《朱子语类》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宋儒的知行理论中,其实知跟行是分离开来的,二者存在先后轻重的区别。朱熹看到了这种分离,并试图通过外在的、形式上的调和来使它们统一在一起,所以才说“用功不可偏”。
但是,知、行既然本质上是对立的,那么学者在用功的时候就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偏离。有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犯了陆象山批判朱熹的那种“支离”之病。因为天下知识无穷无尽,必待认识透彻才去力行,那只会把人培养成两脚书架、书呆子,全不肯着实躬行。另外还有一种人执着于力行的重要性,因而撇开了认识,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最后也只是冥行妄作。
王守仁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弊端,所以他转变了宋儒看问题的视角,他不是从分离的角度去看知行关系,而是采用了同一的角度。他教导弟子徐爱说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对立,而是要从“本体”去看,发现内在的统一。
王守仁说:“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闻到臭味会让我们感到厌恶,其中闻到臭味是知,感到厌恶是行。如果我们没有闻到臭味怎么会感到厌恶呢?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厌恶,就说明不知道闻的是臭味。因此,知规定着行,行也规定着知。此正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犹如身体受寒会感到冷,肚子饥饿会感到痛,受寒与饥饿是知,冷和痛是行。如果不受到严寒和饥饿,怎么会感到冷和痛?反过来,如果不感到冷和痛,怎么知道是受寒了还是饥饿了?
在答顾东桥的回信中,王阳明还举例说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才知道吃东西,“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很明显,读过《实践论》之后,我们会发现王阳明其实是错误的,他把感性认识当作了知,而把理性认识视为行。感到厌恶、感到寒冷和饥饿其实不是力行,而是心里的判断和意志,并不是身体的实践。“一念发动处”和“意”确实是“行之始”,但它不等于行,就如静止是运动的起点一样,但静止并不是运动。
所以说,“知行合一”虽然能够深入的认识到知和行的内在同一,但它因陷入意识里面,乃至于用知吞没了行。

王阳明从同一的角度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
知和行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宋儒从分离的角度看知行的先后,并且寻求外在的统一,产生满口道德、言行不一的流弊;明儒则从同一的角度看知行的统一,而且把行融入知中,导致瞑目静坐、空谈心性的弊端。与前两者不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而且认为只能从知推到行,却不能反过来由行推到知,知是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饮食烹饪技术精良于欧美,但中国人对食品消化、生理学等科学一无所知;世人都知道投资用钱的奥妙,但经济学直到近代才出现;我们题字绘画数千年,却不知美学为何物;秦朝时就开始建长城,但工程学远未出现。如此看来,所谓的真知其实远远落后于力行,知识的发展过程相比行动要缓慢太多,如果必待认识完善、知识完备后才能去行动,那一切都要被束之高阁了。
人们畏于古人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至于畏手畏脚。如果颠倒过来,提倡“行易知难”,将大有利于建设活动,能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发现,孙中山和王阳明都反对宋儒的先知后行观点,但他们二者还存在区别。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存在双向联系,能知必行,能行必知;孙中山则切断了从行到知的联系线,能知必能行,能行未必知,不知也能行!这样说虽然能够鼓舞人心,推动人们去从事建设活动,但也会产生因忽略认识而重蹈宋儒“冥行妄作”的覆辙。

宋儒的知行论是一条以知为起点,以行为终点的思维线段;明儒则是以知和行各自为起点,引出指向对方的箭头;孙中山则是行把知包在行里面的文氏图。通过对知行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无论是单从分离的角度看还是单从同一的角度看,都无法对知行关系得出完善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辩证的思维,要理解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明朝遗老王夫之不仅是一名唯物主义者,而且他的思想中还有丰富的辩证法。他的知行学说分布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书中。他也看出宋儒先知后行论的弊端,说它“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这种知行分离的后果,最终会让学者停留在知上而废掉了行;同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因“销行以归知”,最终也会导致停留在知上而抛弃了行。宋明儒者的观点其实都是崇知而废行。
王夫之认为知行是一对矛盾,致知和力行只有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所谓“知行相资以为用”,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各自的用处,结合是它们统一的方面,各自的用处则是对立的方面。如果不结合,就不会有效用,如果本没有效用,又何需结合?因此,“知行始终不相离”,认识要跟实践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
其次,矛盾有主次之分,与孙中山一样,王夫之也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统领着全局。力行可以用来证明知识的用处,知识却无法说明力行是否有用,因为口空无凭;力行还可以验证知识的真理性,知识却无法证明力行的对错,因为真理是主观理论符合客观现实。所以道理十分明白,知离不开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最后,王夫之清楚地说:“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说明行在知之先,行是知的源头、起点,认识来于实践。对天地的认识来自人类的仰观俯察,是手触摸着大地,是眼睛遥望着天空,为大脑提供可思索的经验材料;酒的味道究竟是怎么样,只有品尝过它的舌尖才知道,任何调酒师都只能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其次,王夫之还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用完善后的认识来指导新的实践,会进行得十分顺畅,真是“乐莫大焉”了。

王夫之(1619-1692)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
《实践论》对知行问题的总结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其对*的影响,自不必多言。《实践论》虽无一句引用王夫之,但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其思想内核竟高度的一致。
《实践论》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说明实践是认识的起源及归宿,认识的过程好似一个圆圈,但它从起点开始又回到原点后并不是重复循环,而是超出上一轮的起点,再度深入。因此,认识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超出自身、深入本质的螺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当然,《实践论》还不局限于知行关系问题,它还涉及到认识的发展阶段、真理的检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等问题,这些我们留待日后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