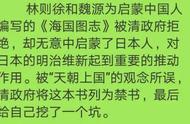维舟
1840年6月21日,英国远征军舰队驶抵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自此将中国拖入了近代的角斗场,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两年后,中国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向英国赔偿两千一百万两白银、上海等五口通商,并割让香港岛。
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全新挑战,自此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难题。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魏源编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到1852年再扩充为一百卷,其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这被广泛赞誉为卓见,在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是家喻户晓,连穿越小说《新宋》也将“长技治夷”作为救亡之策,但问题恰恰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真的能救中国吗?
“长技”的本意
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确实说这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他随后就表明,仅仅这样仍是治标不治本的:“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什么才是最根本的“兵本”和“无形之兵”?就是人心。
孤立地看待魏源的那个命题,可能让我们误以为他是一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的西化论先驱,但通盘来看,就可知他所说的“长技”仅指对方在军事作战上的长处,既未必承认对方科技或思想之优越性,更不见得是要推动整个国家“西化”。换言之,那只是“战术”,而不涉及“战略”层面。事实上,他认为军事挑战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依靠的是从政治和道德上解决“人心之积患”——在这方面,他其实与当时被视为“顽固保守派”的那些士大夫并无本质区别。

魏源
从魏源对战舰、枪炮的估算也可证实这一点:“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既然他乐观地估计二百五十万两白银就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那就明白可见他所说的“长技”仅限于坚船利炮,其主张最远恐怕也不超过洋务运动的范畴。
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师夷长技”究竟何意。所谓“长技”,典出《管子·明法解》:“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竞争的环境下,诸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之类的说法,所在皆是。《孟子·滕文公上》强调,即便是小国,只要取长补短,也能治理好:“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
秦汉帝国统一天下之后,列国纷争的局面转变成了华夷之分。西汉初年的大臣晁错在分析长城内外局势时就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所谓匈奴之长技都是军事技能:“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类议论,后世论政论史多有,如北魏时高闾献议筑城防范柔然:“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魏书》卷五四《高闾传》)唐代对付突厥,也注意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而要战而胜之,办法就是让刘仁恭所部“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以至于突厥人见到都“咸谓似其所为,疑其部落”(《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最终大破突厥,可说是唐代版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明代抗击倭寇,戚继光也提出击败倭寇须“伐其长技”,即打击其长处;后调防北方边境,他又提出“虏之长技在冲突”,指出必须车兵、步兵、骑兵相互配合,如此才能击败游牧骑兵的冲击。天启元年(1621),徐光启主张用更精强的红夷大炮压制后金骑兵,因为“连次丧失中外大小火铳,悉为奴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后金一方,天聪六年(1632)佟养性也陈奏:“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拏火器,以握全胜之势……我国如将火器练成一营,真无敌雄兵,以之威服天下有余矣!”
不难看出,历来文献中所谓“长技”,只不过是考察双方战术中的长处,考虑的重心是如何扬长避短,最终克制对方的“长技”,战而胜之。“师夷长技”通常只是一部分军队采纳战术,并不等于全国上下“师夷”,更不等于承认对方在文明上的优越性,就像西汉对匈奴、唐代对突厥、明代为倭寇,也都既承认其难对付,又继续视之为蛮夷。明正德十六年(1527),汪鋐在借鉴、仿制葡萄牙人的蜈蚣船、佛朗机铳后,在屯门海战中大获全胜,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师夷制夷”的军事家,此后明清也都曾仿制西洋的红衣大炮,但这并不等于以西方为师,更不等于由此尊重洋人、变更国体。
这些史料,魏源都不会陌生,他一生注重实学,讲求“致用”,认为经学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恶夫饾饤为汉,空腐为宋”,强调“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魏源《赠筠谷从兄》)。正因此,他向来着意于边疆史地,就在《海国图志》首次出版的1842年,还曾将著成《圣武记》刻印。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对“长技”的关注只是他务实的表现,但却最多只是在技术层面采纳西方的战术、技艺,他的本意恰恰是要以此来更好地捍卫中国原有的国体和儒家道德。
因此,当他提到“师夷长技”时,所举出的例子就只是诸如康熙曾借荷兰兵船攻打台湾、用耶稣会士建造的大炮镇压三藩叛乱这一类,这与左宗棠1866年提议采用蒸汽轮船时提及清初耶稣会士帮助建造红衣大炮正是同理。更有甚者,《海国图志》中也包含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乃至列举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用来说明土法可“制夷”。
不论如何,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大大低估了西方的挑战,因为问题在于:唐朝可以学习突厥的长技而不被异化,但晚清可以仅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战而胜之吗?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此看法最为冷静:“‘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在已知历史结论的人们眼中格外触目惊心,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但他解读下来的结论是:“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以今日知识来判断,似可认定,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魏源的神话
魏源一生著述很多,其生前最畅销者其实是编定的《皇朝经世文编》,但对后世来说,他的名声主要都是由《海国图志》这一本著作奠定的,而大部分人对这部书所知的又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句话。虽然也早有人发现书中有不少讹误,但大体都认为这是一部巨著,有一种经久不衰的神话甚至暗示:如果当初清廷能像日本那样重视这部著作,本来中国近代史的面貌将完全不一样。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就说:“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确实,《海国图志》在问世之后,因辑录“异邦蛮夷”情形而受主流社会攻击排斥,1858年王茂荫建议将之刊刻重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但朝廷不予理睬,这部书在国内仅勉强刊刻千余册。

《海国图志》
相比起来,《海国图志》在日本被视为“有用之书”,乃至被推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纷纷加以翻译、训解。从1854-1856年仅仅三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就有二十一种,“书价飙升三倍,对维新派思想体系之完善不无推动之功”(刘柠《中日之间》)。日本左翼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现代史》中称:“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民国时钱基博也不吝赞词:“日本之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照此,似乎《海国图志》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甚至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有赖于此。但客观来看,日本对西洋的了解比晚清中国深入得多,其第一本介绍西洋的本国著作是《解体新书》(1774),比《海国图志》的出版早了六十八年。德川幕府1855年开设洋学所翻译西洋书籍,教授外国语文,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蕃书调所”“洋书调所” “开成所”等,成为东京大学前身。在这些方面,日本无疑走在前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当时的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像佐久间象山虽然认同《海国图志》所指出的“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等诸多分析,强调“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的重要性,但他对能否“制夷”绝无幻想。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是士大夫普遍主张的“以夷制夷”的延伸,其前提至少是“夷”有办法可“制”,但日本国内当时普遍的观感却是“连中国都战败,日本更毫无胜算”,佐久间象山所竭力谋求的最好结果,在清朝看来却是最坏的结果:“对等开国”。
1863年初,朝廷督促幕府和各藩上奏“攘夷”的策略,松代藩藩主专门向佐久间象山问策,却得到一个冷淡的回绝:“攘夷”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不可能想出具体策略。他在回信中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想出具体策略,即使去问松代藩传说中的英雄真田幸村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哪怕是诸葛亮再世、孙子复活,也不可能想出“攘夷”的具体策略,因为“两国相战,我之国力不及敌国,纵使我之德义远胜于彼,亦难以得志。此即天下之正理、实理、明理、公理也”。在他看来,儒学者都是无用的存在,他提出的著名观点“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其中前者仅指忠孝的重要性,而后者却涵盖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础的工学、军事科学等应用科学,比魏源所说的“长技”深入得多。
这意味着,在面临西方挑战时,中日两国原有的政治结构、社会心态、思想基底乃至危机意识都很不一样,因而对《海国图志》的价值认知也迥异。即便这本书对明治维新有所推动,真正关键之处也不是书本身,倒不如说是日本社会已经做好准备接纳书中的思想和即将到来的变革。单靠一本书根本不足以引发变革、有效应对列强的挑战,就像数十年后梁启超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推崇备至,但驻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则讥讽说,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
《海国图志》在国内的处境表明,魏源的思想无法在那样的环境中留下建制性遗产。更重要的是,魏源自身其实也难以挣脱儒家传统的框架。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常使人误以为他主张“技术现代化”,研究中国军事史的欧阳泰甚至称他是“主张西化的著名先驱”。事实上,他虽然强调实学,但仍以规复三代之治为目标,因而宣称:“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他绝不是要“西化”,只不过强调要务实地研究实现“王道”的手段,但对“王道”本身的信念十分坚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默觚·治篇一》)
他和那些“顽固守旧派”有一个共识:解决整体危机(包括“制夷”)的根本在于“人心”。被视为守旧派代表的倭仁就曾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差别只是,倭仁认为应当专注于“礼义”和“人心”,而魏源则认为“权谋”和“技艺”也不可偏废,但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其实也完全适用于他:“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在这样的视角下,洋人的“长技”往好里说也只是为了补益“王道”的手段。晚清堪称最深刻了解西洋的王韬,公认其改革建议已超越了单纯的洋务论,在《弢园文录外篇·变法中》更提出师法西方:“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这类所说的“师其长”就已不再只是战术,而变成了谋求富强的治国术,以导入西洋机器强兵为首,兼及取士、练兵、学校、律例,但他也仍然坚称:“且此之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与往昔者也。”(同书《变法自强上》)因为“孔子之道,人道也”,是“不可变者”。
直至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等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才呈现出新的面貌,而此时对“西人之长”的理解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教育家蔡元培提倡兼容并蓄,将现代描绘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强调在艺术领域也大胆取人之长:“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之长,我人独不采用西人之长乎?”这就使得人们更容易在回溯时,将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误认为是提倡现代化的先驱了。
但回到他所处的历史语境来说,魏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将自己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试图从实务入手,锻造一个能更有效应对内外挑战的国家。孔飞力在《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中对他的评价是中肯的:“魏源那一代的改革活动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治国从政的具体问题上,他们的目标是实行经世致用的治国之道,而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至于那个先驱者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后人在“从后往前读历史”时建构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魏源。
责任编辑:于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