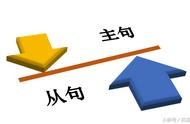在冷战胜利之后,自由主义者似乎失去了自己曾拥有的历史感。这使得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腐烂到一半的木头中的真菌一样,后自由主义者似乎一直被踩在脚下。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的攻击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他们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一种破坏传统并压迫那些不符合其规范标准的人。这些攻击清楚地表明,自由主义者必须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以及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中各种变体是多么重要。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致力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被视为是与生俱来的,超越了文化、性别、国籍或任何其他特定情况。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悠久历史中,对于如何最好地实现人类的解放存在许多分歧。一些人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确保自由,另一些人则认为严格的法律框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有一些人认为所有政府都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这些分歧形成了相互竞争的自由主义思想流派。
思想的分歧是如此的多样化,以至于人们常常觉得对自由主义的解释与自由主义者一样多。但如果我们拨开争论的迷雾,我们可以将自由主义缩小为两个相互竞争的阵营:多元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定义了我们的现代生活,而真正的人类繁荣的未来则取决于其中的胜利者。
自由主义分裂的根源
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是在欧洲有机地发展起来的,作为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办法。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将西方社会团结在一起,将不同的王国和部落团结起来。在新教改革之后,这种社会统一性崩溃了。一旦因信仰而走到一起,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欧洲很快就陷入了血腥的宗教战争。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这场纷争。
在自由主义传统的早期信徒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欧洲社会裂痕的方法。对于许多改革者来说,特别是在英国,解决这些文化分裂的最好办法是将人类利益的问题留给地方机构和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个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政权的更广泛目的变成了确保这样一个多元化和复杂的社会蓬勃发展所必需的自由思想。在这个方向上最有名的举措是《大宪章》,但代议制政府、行会和集会主义宗教的兴起都源于这种自由主义的冲动。
而其他自由主义者——例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认为教会的霸权只有通过将启蒙价值观传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才能被取代。在这种观点下,地方机构几乎没有自我管理的空间,因为这些机构通常非常热衷于坚持中世纪的价值观。因此,对于这些开明专制主义的倡导者来说,能够真正传播平等、自由、财产权和宗教宽容等自由主义原则的唯一工具就是国家本身。
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政治实践并没有发生冲突。一个是源自人民本身发起的大众运动,而另一个则是来自于上层的强加。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共同努力打造了自由文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相互矛盾的自由主义立场开始分裂成两种独立的分支。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如约翰·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伊曼纽尔--开始选边站。作为这一思想争论的产物,自由主义传统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多元自由主义和国家自由主义。
多元自由主义多元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对社会和现代世界复杂性的欣赏:个体是多样的,文化是复杂的,大多数重要问题都存在深刻的争议。多元自由主义者没有涉足混乱之中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案,而是强调让个人去在他们的地方机构(例如学校、教堂、医院等)寻求社会力量,这些机构介于公民和国家之间。正如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言:“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美好且有益的社会和经济实体。他们认为,这些自愿组织的私人协会的力量......是民主社会的大部分力量之源。"
近年来,多元自由主义在美国呈现出两种形式。一个更左倾,一个更右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和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最好由政府完全从人类日常生活所面临的问题中退出来。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政府的工作只是保证所有人的消极自由——不受约束的自由。
更左翼的多元自由主义受到像前面引述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的人的拥护,他们认为政府在活跃的“the little platoons”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多元自由主义者支持社会福利制度和资助学校,而不考虑其宗教信仰。

国家自由主义译者注:“the little platoons”是民间的志愿性团体或中间团体,它是民众培养兴趣爱好,锻炼自治能力乃至参与社会治理的天然场所。
多元自由主义者强调多元化和在复杂社会中实现自由的重要性,而国家自由主义者则专注于将国家政治机器作为人类解放的关键。他们的核心信念是,只有通过将政府的参与大规模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人类的自由才能进步和持久。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执行使自由成为可能的原则。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大英帝国的官僚主义欺凌是国家自由主义最臭名昭著的时刻。尽管它在许多情况下扮演的角色更加模糊,比如凯末尔主义时期的土耳其。在美国,国家自由主义在进步时代流行起来当时在许多人看来,只有政府的力量才能充分挑战腐败行业的暴政,这是可以理解的。最近,"伟大的社会 "将美国的国家自由主义扩大到不仅试图大幅度地重塑经济,而且试图重塑社会本身。

译者注:伟大社会(英语:Great Society),或译为大社会计划或大社会,是在1960年代,由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其在国会的民主党同盟提出的一系列国内政策。1964年,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由此所提出的施政目标,便是“伟大社会”。主要目标是经济繁荣和消除族群不平等。
事实上,自由主义传统既需要它的国家主义倾向,也需要多元主义倾向。人类只能在较小的社区中才能获得有意义的自由,但如果没有政府对某些权利的保护,这种自由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自由主义政治往往必须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之间取得平衡。当多元主义发展得过于强大时,政府必须介入以保证个人权利。当这种对权利的保护开始超越其基本任务并侵蚀中间机构时,那么国家就必须受到约束。
近年来,美国已经失去了这种平衡,国家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这种看似国家主义冲动的胜利是一种对现代政府的绝对复杂性的自然反应。正如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 )在他的巨著《论权力》中所论证的那样,现代战争和社会需求几乎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普遍去相信,只有一个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国家才能解决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安全。近年来,我们所经历的许多国家权利的扩张被合理化为试图给自由民主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工具,以抵御极权主义的敌人。
更容易理解的解释是,现代国家的权利扩张旨在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在二十世纪末,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中大部分民众受到过怎样的诽谤和虐待。简单地说:尽管这些国家可能致力于人类解放,但这种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延伸到国内各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少数群体。对于许多自由主义改革者来说,国家权利成为唯一足以确保这些群体的权利不被当地社区、宗教组织或政府本身剥夺的机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开始不断努力规范和消除每一个细微的歧视。
国家权利的这些扩张中很多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为推进自由主义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在没有强大的多元主义对手的情况下,向国家自由主义的倾斜开始破坏它试图促进的传统。国家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非但没有推动解放和进步,反而导致了公民社会的崩溃。正如一些社会科学家所显示的(最著名的是罗伯特·普特南),站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机构正在枯竭。其结果是,人们被孤立感所困扰。简而言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元化的自由主义。
复兴多元自由主义之路那么我们如何恢复多元主义并重振自由主义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简单的答案是最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寻求削弱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监管权力。实现这一巨大变化的关键是政府采用由荷兰神学家和政治家亚伯拉罕·凯波尔精心设计的独立领域模式。

在美国,自由主义者们完全致力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必须塑造一个 "中立 "的公共空间,不拥抱任何主要的文化或宗教传统。虽然这当然是多元自由主义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它也不是最好的方式。许多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这种努力完全是徒劳的,现在看来他们是正确的。
凯波尔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其允许每个文化派系创建自己的医院、学校、慈善机构等。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团体都有权获得平等的政府支持,并在宪法的范围内被允许完全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个独立领域模型的天才之处在于,最能影响人们生活的决定——学校的类型、选择的医疗、处理周边的自然资源等等——将在由当地来处理,由在这些机构工作和参与的人处理,而不是由联邦政府。其结果是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参与到他们周围各种机构的运作中。
许多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独立领域模式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这只是赋予了地方机构歧视少数民族的权力。虽然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禁止彻底的歧视同时,仍然允许地方机构有大量的回旋余地来定义自己。比方说一所学校必须接受所有学生,无论其个人背景如何,这并不意味着要规定学校应该提供什么课程,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政府来决定。
简而言之,独立领域模型赋予社会中“little platoons”再次自我管理的权力,同时仍然有可能在这些机构内惩罚公开的反自由主义倾向。这样的倡议只是恢复多元自由主义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这是一条值得走下去的路。因为如果我们成功地驾驭它的曲折,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多元化社会存在的乐趣。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既能管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又能与那些与我们根本不同的人共处并学会欣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