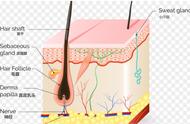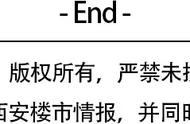这故事发生在1935年。河北省有个杨格庄,庄外一片米粮川,全都是恶霸地主“积善堂”黄家所有。
老佃户杨白劳,一世的牛马生活,已熬得身体干枯如柴。他老伴已去世多年,只剩下闺女喜儿,今儿也随着爹下地收秋来了。
杨白劳看着闺女钻在齐腰的谷丛里,拼命挥舞镰刀;听着她“呼哧呼哧”喘粗气儿,不由一阵心酸:“喜儿,晌午了,看你累的。”
喜儿站了起来,这是个多好的姑娘。她抹了把汗,笑着说:“爹,你先歇着,我把这块割到头,大婶也该送饭来了。”
说话那会儿,王大婶送饭来了。他们都是黄家佃户,喜儿和大婶的儿子大春早已订了亲,两家人如同一家人。虽是如此,杨白劳还是忙不迭地向她道谢。
喜儿叫了大春来吃饭,快到田边,喜儿突然站住脚,不走了。原来给黄家看羊的赵大叔来了,正和杨白劳、王大婶说着给他们完婚哩。
三个老人的谈笑,陡地都住了嘴。原来“积善堂”少东家黄世仁和管家穆仁智,坐着马车,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
黄世仁一见喜儿,便死命盯住看。穆仁智心领神会,连忙勒住马,故意喊道:“喜儿,割谷哩?”喜儿扭过头,睬也不睬。
杨白劳忙赶过来打招呼。穆仁智却半嘲半笑说道:“老杨,你糟践人呢,这么好的闺女,当牲口使唤。求求少东家借个牲口使使不成?”
大春挑谷过来,听见穆仁智不三不四的话,早窝足了火,一眼又见黄世仁的马车牲口在吃庄稼,火更大了,抽出扁担就是一下。
穆仁智瞪起眼睛想骂,被黄世仁阻止了,于是扬鞭打马,一溜烟儿跑了。大伙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黄世仁在车里,还一直探身望着喜儿,直到跨上“积善堂”台阶,他一双贼眼还回头瞅了瞅。
黄世仁见过娘,兴致勃勃地说:“娘,你看,你眼睛能望到的庄稼都是咱黄家的,这是10年不遇的好收成!”但老太婆捻着佛珠,头也没抬。
过了半天,她起身要去佛堂上香了,才关照穆仁智:“老穆,今年佃户收的粮食多,收租时要多长点心眼,多年的旧账该清一清了。”
老太婆一走,黄世仁立刻捋起袖,喝叫:“老穆,把账簿拿来,查查杨白劳欠多少?”
谁知杨白劳竟不短租子。往年陈账倒有一笔,计25元,可是按照老规矩,到腊月门上才满期。黄世仁不禁叹口气,一甩袖子背过了身。
穆仁智早看透了黄世仁的心思,悄声说道:“嗨,这可是怪我没长心眼。少东家,这事交给我,到了腊月门上,我一定叫你见人就是。”
谷子登场的时候,穆仁智收租来了。可怜杨白劳一年的劳累,自己只留下几斗谷子,全给“积善堂”送来了。
杨白劳走进收租院里,看见满院子人都低着头,不说话。一打听,原来老五叔短缴了几斗旧欠,穆仁智就把他种的地给抽掉了。

老杨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也有旧欠呀!忙向前哀求,请穆仁智高抬贵手缓个期。穆仁智扫了喜儿一眼,竟堆起笑脸答应了。
晚上,老杨怀满腹心事,在豆油灯下抽烟。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哭声。王大婶和大春走来告诉他:老五叔跳井了!
老杨“咳”了一声,一屁股蹲下来:“老天不睁眼啊!咱穷人就只有这条路吗?”
屋里鸦雀无声。半晌,王大婶才说:“他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了,好歹我们还有两个孩子,拼死拼活,怎么也把今年的利钱凑齐,把账顶挡过去。”
为了腊月门上的利钱!不管风霜雨雪、天寒地冻,不管峭壁千尺、谷深万丈,大春和喜儿天天都进山砍柴。
为了腊月门上的利钱!王大婶和杨白劳两亲家,也一刻没有闲过,一个在家磨豆腐,一个出去叫卖。
岁尾的时候,喜房抹好了,利钱也挣得差不多了。两家四口人,看着手中的银子,都不禁舒了一口气。
除夕那天,老杨和大春挑着柴火、豆腐担子去赶最后一次集。
柴卖了,豆腐也卖了。老杨算来算去,凑足了利钱,只剩下几十个铜子。他叹口气,对大春说:“你去称二斤面吧,今晚上大伙吃顿饺子。”
老杨想着明天是喜儿大喜的日子,该给她买点什么,无奈实在没钱,只得买了两朵红绒花、两尺红头绳,交给了大春,自己就到黄家交利钱去了。
大春兴冲冲赶回家,悄悄把绒花、头绳往喜儿手里一塞。喜儿又羞又喜,一扭身,钻进了喜房。
虽说只是一对绒花、几尺头绳,喜儿心里却暖洋洋的。她马上对着镜子梳起头,剪起窗花,还悄悄儿唱起来:“鸟成对,喜成双,半间草屋作新房······”
就在这个时候,杨白劳跌跌撞撞跨进黄家大门。一进门就碰上穆仁智。穆仁智皮笑肉不笑道:“老杨,来得好,我正要去找你呢!”
进了暖阁,见了黄世仁,杨白劳抖着手掏出七块五毛银洋,恭恭敬敬放在桌上:“少东家,今年的利钱我是一个不短啦。”
谁知黄世仁哼了一声,说要本利全收。老杨急了:“少东家,就这还是拼着命挣来的。今天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的骨头,也拿不出呀!”
黄世仁刷地变了脸:“欠债还钱,有什么多说的!”杨白劳不由呆了。这时候,穆仁智阴森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老杨啊,把喜儿领来顶账吧!
老杨一听,身子都瘫软了:“少东家,这不行呀······这万万不行呀!”可是,黄世仁就像没听见似的,喝叫穆仁智快写文书。
老杨又急,又怕,又恨,喊道:“你们不讲理,我…………我找讲理的…………”穆仁智冷笑道:“哼,谁不知道,少东家就是二县长,黄家就是衙门口。”
黄世仁也在一边吼起来:“好啊,讲理!老穆,别和他噜苏,叫人把他捆起来,送到县上讲理去!
狰狞的面孔,咆哮的声音,把老杨吓昏了;他被穆仁智捉住手,在文书上按下了手印。

没等老杨清醒,文书已经到了黄世仁手里。他得意地嘿嘿笑道:“送他出去,叫他明儿送人来!”
老杨被拖出门外。风雪里,两只石狮子座,也好像张牙舞爪,要向他扑过来。
杨白劳慢慢清醒过来,他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幕,愤怒地扑上去。可是,那两扇兽面铜环、铁皮包裹的黑漆大门,一动也不动。
老杨不知如何是好,坐在黄家门前,伤心落泪。恰巧老赵走过这儿,以为他受了财主的气,伸手把他拉了起来,伴着他回去。
家里的人正等着他吃饺子哩。老杨回到家,喜儿高兴得什么似的,又蹦又跳。老杨的心啊,如同刀绞一般。
老赵是个乐呵人,张罗着要喝酒。又把大春和喜儿叫到身边,说:“你爹受了财主气,心眼窄,想不过来,让他闷会儿,我先来讲故事给你们听。”
他又说起那经常讲的红军故事:“那是民国20年,你大叔给财主家逼得实在活不成了,就担着一担辣椒,奔了黄河西岸。
“到了陕西保安县马家沟,一天黑夜,我宿了店,正在脱鞋上炕,忽听村外乒乒乓乓地响开了。伙计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
“红军一到,这世界可就变了样。第二天一早,那地主大院里,压在大伙背上的文书老账,一把火都给烧了。
“接着又分了地,家家户户有地种,可把老佃户乐坏了。嘿,我真是头一回看见有这么个地方。”说完了,老赵还出神地回想着。
这故事,大春和喜儿都听过不止一次了,但他俩仍听得像着了迷。大春问:“红军在哪?”老赵说:“过了黄河就有。天不转地转,总有一天会来的。
夜深了,明天要做新娘的喜儿,没注意爹爹的神色,她伏在爹的膝头上,感到爹爹今夜分外亲切。
喜儿甜甜地睡着了。老杨含泪把她扶上了炕。听她蒙蒙眬眬喊“爹”,老杨再也忍不住,那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啦啪啦往下掉。
“喜儿喜儿你睡着了,爹爹喊你你不知道。你做梦也想不到呵,你爹有罪不能饶!
“你娘临终嘱咐我,好歹要把你拉扯大。可如今我糊里糊涂卖了你。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我得去找黄世仁!
拉开门,一阵狂风夹着雪花扑来。老杨恍如看到黄世仁凶恶的脸,犹如听到穆仁智狠毒的话:“少东家就是二县长,黄家就是衙门口.····.”
再没路可走了。“黄世仁呀,你是要我死!好,我死!”他转身奔回屋里,抱起墙台下的卤罐,一仰头,一气灌了下去。
丢下卤罐,杨白劳脱下身上的棉袄,加盖在喜儿的身上,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喜儿呀,爹······爹不能管你啦!
“黄世仁呀黄世仁,你伤天害理不是人,我我我,我死也不能饶了你······我要死在你黄家大门前·····.”
漫天风雪,路上没有一个人。杨白劳跌跌撞撞走向“积善堂”。远远已看见那高大的门楼,这时,卤毒发作了。
纷纷大雪不停下着,似乎要掩了人世间的不平。可是,它盖不了老杨的仇恨,他的眼睛到死都睁得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