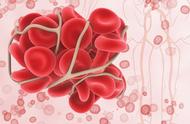作者: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各种新情况和新现象层出不穷,给我们认识社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调查研究是深入社会现实、抓住现象本质的重要手段。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明确指出,调查研究“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调查研究中出现形式主义,除了思想态度上的原因之外,对于调查理论和方法的认识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是社会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结合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实践,对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阐释,希望能够帮助调查者达到一种“方法自觉”,推进调查研究的运用和发展。
社会调查是伴随着社会学学科的产生而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学者回到国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在建立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同时,大力推动社会调查的发展,从北平人力车夫调查、居民生活费调查,到定县社会调查、无锡保定经济调查等,掀起了一场引人瞩目的“社会调查运动”。在此基础上,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力的学者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引进英国文化人类学、美国芝加哥人文生态学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社区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社会调查运动”相比,“社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更进一步,主张选择一些相对固定的社区(在中国最为典型的就是村落)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和历史的研究,这有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的本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在华北和西南地区开辟了多个社区研究的田野地点,诞生了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产生了以《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为代表的社区研究的典范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费孝通《乡土中国》这样的理论著作,深刻把握和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在费孝通等人的主持下得以恢复。在重建过程中,费孝通大力倡行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通常也将其称为田野调查,是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拓展。费孝通身先士卒,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学学科始终以“从实求知”作为学科准则,走出了一条紧贴中国社会现实、反映中国发展经验的中国社会学道路。“从实求知”是费孝通对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的概括,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主要是如何通过调查实践来处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达到对社会现实客观而深刻的认识。
在学术研究的实践脉络中,田野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主张。有些学者会主张抛开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成见,“拥抱”并忠实、客观地反映在田野中感知的事实,认为这样才能在“实证”中推进学术研究,强调调查本身所带来的“经验感”“现场感”对研究的启发作用。也有学者强调理论在田野现场中发挥的作用,并认为,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尽管调查者自以为客观地反映了事实,但充其量只是收集了一些声音影像或意见态度,这非但无益于我们认识真正的社会事实,反而可能会误入歧途。这两种主张走向极致,都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真实性,有学者分别将其称为“朴素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朴素经验主义讲究“眼见为实”,将田野中收集的材料当作研究的结论,缺少分析辨别之功,会将研究变成“报告”或“报道”;抽象经验主义则从理论出发,去田野中挑选与理论相应的材料,或者用理论“裁剪”现实,田野变成了理论的工具。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论文,机制分析、结构分析琳琅满目,概念框架和逻辑框架严谨自洽,用抽象的语言讲一些现实的问题,会走向一种貌似高深的肤浅。但事实上,田野调查并非只能产生这两类研究。
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是社会科学面对的普遍问题。理论如何在田野中“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起作用,既能帮助调查者洞察社会现实,又不喧宾夺主,用理论剪裁现实?“从实求知”原则所强调的要义在于,理论是调查实践的工具,现实是调查实践的目的。费孝通在解释“从实求知”的时候说:“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
可以看出,费孝通所理解的“从实求知”正是要求社会学在田野调查中弥合、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所谓“再回去”,所谓“图报”,是为了求得真正的“知”。调查者要以调查对象的感受、思想、行为和命运为研究目的而非工具和手段。这是费孝通对吴文藻提出“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的社区研究法的升华。吴文藻所说的调查目的还是“实地研究”,而费孝通直接就说“回到人民”,这是田野调查方法的新论,也是费孝通一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结晶。田野调查方法既不是各种调查设计框架,也不是各种调查技术技巧,而是在田野中如何做到以理论为工具、以人民为目的方法。
调查者在进入田野时,既带着充实的理论,又不被理论所支配,就需要有充分的“方法自觉”意识。所谓方法自觉,就是要在田野中保持强烈的反思意识,即我们在观察访谈一个人、在讨论追索一件事的时候,到底依靠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工具。这种理论工具犹如黑夜中的探照灯一样,让我看到并洞察到某些东西。理论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既可能是深刻的本质,也可能是理论的偏见。当我们看到某个现象与我们的理论不一致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个现象看作表面的、暂时的。例如,我们用资本理论去观察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时,如果发现他们很融洽,没有支配和剥削的关系,就会认为他们是隐瞒了什么,或者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观察到。在理论潜意识的支配下,我们会直到找到一些“剥削”的蛛丝马迹才罢手,并认为这是穿透了社会现象的表面而进入到深层的结构,找到了社会的“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到底是理论的真实还是现实的真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反向追寻我们的研究过程,对其做一个方法论上的检视。其中的关键步骤是,我们所忽视的、要“跨过”的那些社会现象到底是因为与理论不一致而被“表面化”的,还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浮泛的、暂时的,并无扎根于其中的结构作为支撑?我们有没有对其深入探究,以研究对象自己的逻辑来理解这种现象,还是仅仅因为我们的理论而将其忽略掉呢?
有些学者提出要注意事件和人的“边缘”或“变态”(相对于中心、常态而言),还有些学者指出要注意田野中的“异例”(相对于典范、典型而言),这都是田野中“方法自觉”的体现,是田野调查中突破“理论障”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除了要求调查者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之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最好在田野的“现场”中展开。田野调查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调查者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或者沉浸到田野中,除了用耳目口鼻之外,还可以用“心”去感觉、感受调查对象的思想言行,用“感通”去直接把握调查对象的深层要素。还是以上述老板和雇员关系为例,那种“融洽”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与研究对象的“感通”。这种感通好像是一种方法,但归根到底并不是方法,它的发生需要很多天时地利的外部条件和机缘,而田野所能提供的往往就是这些条件和机缘。有了田野之后,能否感通,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从实求知”的调查理念。以调查对象为调查目的,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为目的,而不是以理论或者研究论文为目的,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从实求知”。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