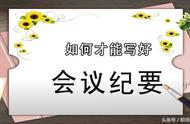我立在这道坍圮的灰色墙下,轻轻抚摸着它粗糙如枯松皮的皮肤。岁月剥落了它曾经年轻的容颜,带走了它或者曾有的巍峨。
只有一株孤单的爬山虎,却仍将其苍翠附着在它不算宽厚的脊背上,并仍奋力向上攀爬着。此外,便唯见墙根上死咬着的一片片青苔。不见许多生机。
它曾经是什么模样的呢?或者它的主人,也曾将朱红的漆做了它华美的衣裳,以鲜亮的琉璃瓦,做了它的可人的冠儿。人们或者也曾在其身边驻足,欣赏它华美的衣裳上的花纹;也曾抬头,遐想它身后那雕梁画栋,美室华屋。
大约,它也曾聆听了身后高屋里曾传来的丝竹管弦,欢声笑语;大约,它也曾享受过身后曾投射过来的或柔和或繁华的灯光;大约,它也曾记载下身后曾有人享受过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然而,兔走乌飞,白云苍狗。它身后的浮华,不知何日弃它而去,唯余黄土无数,荒草恣肆;而它自身的绮丽,也不知何时悄然消散,唯见缝隙丛生,伤痕累累。
然而,所幸,爬山虎还在的;青苔也还在的。而且大约春来的时候,那些莫名的藏在墙头泥土中的种子,会开出鲜丽的不知名儿的花儿来;斑斓的蝴蝶也会来,为它添彩;小巧的黄鹂也会来,为它歌唱。我想,那时,它肯定是以最美的姿态活在这人世间的,比它初生还要美上一百倍。
我的思絮飘飞了许久,小孩子过来了,欢笑声将它们拉了回来。“叔叔,你在看什么呢?”一个孩子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那双眼睛很纯净。“叔叔,你看到那苍翠的爬山虎了么?它们在给断墙清扫灰尘呢!”另一个孩子说。
我点点头,感觉那语言也很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