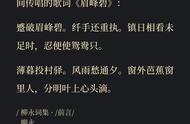文 | 冯彦伟
古窑村的封存,或多或少地还留下了些许古城陶镇的遗迹。古城博山陶镇的老居民区,有点象迷宫,匣钵铺就的曲折折小路,紧贴的便是匣钵砌成的墙,黑褐色蛇行,眼见得此路不通了,忽又旁逸斜出,在人家咿呀作响的窗户下挤出一席之地来。每天走来走去,童年的乐趣多是在这捉迷藏般的游戏里度过的。

因为谋事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城里。北京的王府井,济南的大观园,上海的南京路,甚至风光独特的广州最古老的沙面岛,人说是个文人能来灵感的去处,即使心血来潮绕有兴致地匆匆而过,也隐隐约约地感觉与其堂而皇之于繁华街市,道不如静思于古道、老巷、四合院耐人寻味的多。
在我看来,几乎都是如此,只因为在外小住,是大城市与故乡之间,事业与亲情之间的逗号,常常生出一些心神意乱的情绪。京城虽去的多,但往往自以为是,几乎都懒得去走一走,真正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深层次地去认识似乎很少。窗外,一伙伙放学归来,行走在老四合院街头的学童,令我想起陶镇的老街,充满人情味的古道。
生于陶镇,或者曾在陶镇的古圆窑里构思过关于陶的作品,那里头的家什玩物,都在我的记忆之外。不曾为他们打动过,这与它曲曲折折的走廊有关。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些匣钵砌成的里弄小巷里,走进匣钵的老屋,靠墙角便是用匣钵做成的烧火炉子,那炉子也算作民间艺人的造化,是古圆窑的延续和缩小,底部有炉盘,中间是灶堂,堂外便是一个倒扣的匣钵,离灶堂约寸指。旁边便是灶口,也是用窑泥做成的烟囱,直接屋外。冬天可以取暖做饭。因此,天再冷给人们带来的都是温暖。

近几年的旧城改造热火朝天。对过去许多城市的孤独感也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家乡,看看眼前的一切,过去的小镇早已面目全非,也在临摹着现代城市的样子,弯曲的小道拓了又拓,直了又直,小城的窑顶正象放了规、矩,按现代化的书本放着大样,道中的隔栏,警告人们不得翻越;斑驳的线条,指示人们顺利通过,中间的黄线告诫不守规矩的人那是一堵墙,人是不能在墙上走的;倘若不是古窑村的构想,显然人们再也找不到匣钵下的街道了。

往往,有的当失去的时候,方才感觉存在的价值,也由此更感未曾有心阅历某些城市的过失。其实,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去看,更平添了生活丰富的内涵。就京城与陶镇而言,陶镇受北京文化的影响就十分的明显。因墙的存在,便有了胡同的叫法。更因起联想的是陶镇的一些古老的街道都叫什么“胡同”,而这种取名除与北京类同,在其他城市都是极为罕见的。
博山陶瓷生产合作社的初期,就设在南北胡同之间,附近还有蒋家胡同、陈家胡同、钱窑胡同,联想到北京的若干条胡同,认为陶镇是从北京移植的街道命名。据考,北京把街道称为胡同,起源于元代。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记述元大都“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这“火巷”就是《元经世大典》中所记的“火弄”,清翟灏《通俗篇》称:“‘弄’实古字,非俗书,其音义皆与‘巷’通”。明谢肇制《五杂俎》考得“火弄”后来被讹传为“胡同”。前人也考证认为,“胡同”二字确切地说是蒙语,是蒙语“浩特”的音转,其含义指居民点、村落之意。

元代北京的“三百八十四火巷”即指“胡同”。“胡同”一名元杂剧中已出现,如《沙门岛张生煮海》里,梅香就说:“我住在砖塔胡同。”北京至今有砖塔胡同,证明已存在800多年了。北京的胡同取名五花八门,有雅有俗,极雅的有“百花深处”,极俗的有“羊尾巴”“猪尾巴”等。陶镇旧有的许多条胡同的命名,就是摹仿北京而来的。北京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如“魏家胡同”“方家胡同”,陶镇就有“宋家胡同”“蒋家胡同”“李家胡同”“高家胡同”等等;北京有“赵家井”“罗家井”,陶镇也有“甜水井”“蒋家林”“墙后”。胡同作为街道名称,是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陶镇的借鉴而效仿,与其陶瓷生产不无关系。陶瓷产品销往京城,文化信息的传播,都必然受到北京文化的影响。

陶镇的老街,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它是留在我脑海里抹不去的生活情结。也只有那些从老街上走出去的人,才会这么深深地念念不忘,不忘那古圆窑、四合院、小煤炉的好处。老街,变成了小城,旧瓦房变成了大楼房,四合院变成了大观圆,小胡同铺成了柏油路,古陶镇变成了新陶城。虽然,这里的胡同已经不见了,赋予了现代意识的街道名称。但是,北京文化的影响不会减退,因为许多新的道路、新的建筑和新的生活观念,受北京的影响会更加的深远。
不是舍不得老城的过去,而是念念不忘那老街的情怀,怀念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来源:博山的故事)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