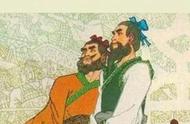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的书籍中,夹着四年前的一张请柬。自香香同学郑重其事地呈到我手中后,我就一直保存在这里。有时候,坐在书房里看书写文或批阅试卷疲倦时,抬抬头就能准确地知道它的位置。我总会出神盯上一会儿,微微一笑,凝神继续先前的工作。
香香是我十几年前在镇中教书时的学生。我是她的数学老师。由于在学校担任了一个行政职务,平时学校管理工作非常繁忙,我总是上完课拔腿就走。以以致于初一上了几个星期的课,班上的同学我叫不出几个人的名字。
有一天课间休息时,我坐在办公室喝茶看一份校长室转来的文件。一个小女孩在我门口晃了一下。我抬头看门口,没发现人。我便低头继续看文件。就听门口传来低低唤老师的声音。我走出房间,见一女学生怯怯立在墙角,拿着一本书抬头紧张地盯着我的窗户。我招呼她进办公室,尽量消除她的紧张感。过一会才知她的来意,有一道题不会做。在给她讲解这道难度比较大的题的时候,我惊讶于她的思维敏捷以及她的逻辑严密。我笑着问她的名字。出乎意料,她白了我一眼,嘴角一扬,我分明感觉出她的气愤。她把书的封面翻开,我看到雪白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写有她很秀丽的名字。我记住了她叫香香。走出办公室时,她大声说你真该到班上多去走一走。我听后猛地一怔。

我以前也曾当过几年班主任,与学生关系很融洽,只是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后就不再当班主任了。也总借口事多踩着铃声进出教室,与学生交流得很少。香香的话一下点中我的要害,我不由得盯着走远的香香,高看了她一眼。
后来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强迫自己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上课前后都多花一点时间在班上呆一呆,上课时语气尽量亲切幽默些。我的这些显著变化自然得益于香香同学的提醒,也逐渐形成为我的教学习惯和教学风格,一直保留到现在。
香香衣着朴素,从未见过她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入校。她课后总与同学大声谈笑,或是争论题目,辅导同学写作业,走到哪里都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然而上起课来,神情极为严肃,扑闪着一双大眼,仔细盯着黑板,不疏忽一个细节。放学后我在学校总是走得较晚,很多次路过班级时,总会发现她要么在班上写作业,要么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要么摆放桌凳把教室整理得清洁整齐。
在香香初二下学期的暑假,她的班主任调到城北一所新办的学校去当了领导。送走这位与我搭班十年的亦师亦友的老同事,我倍感失落。这个时候,镇中已经开始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了。差一点我也心动就想离开镇中另谋发展。夏日的一个上午在城南小巷的石板路上行走时,碰到香香和班上几个学生,眼巴巴地看着我,异口同声地问起我是否也要离开镇中。就在刹那间,我忽然坚定了信念告诉这些学生,我不会这么快离开这里,至少也得把你们带毕业。学生们欢呼雀跃而去,我却沉默不语。

我自然而然接下了香香读初三时的班主任工作。因为是毕业冲刺的一年,我对班级管理得非常严格,学校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学生的成绩一天一个样地不断提升,学习状态也很不错。
有那么几天,我总感觉到香香精神恍惚,读书无精打采。问问周边的同学,没人清楚原因,问她自己也支支吾吾。直到有一天整个下午她都没来上课,我决定到她家去家访。
依着通迅簿上的地址,我在城南曲折的小巷深处寻到了这个破旧的院落。我不敢相信城市里还有这样破败的房子:四壁空空,鲜有几块完整的青砖泥土垒起的瓦房,正大门一堵墙只用几块黑旧的木板钉着,有很大的缝隙,最上面一排用街上做广告的旧塑料纸粘贴住,几挂茅草塞在墙角飘动,我能想象刮风下雨或是寒冷的冬天时我的学生在房子里生活得如何艰难,甚至能想象她端着碗筷缩在寒风里吃饭的样子。当了她两年多的老师,我竟然不知她生活环境这般恶劣,我为自己的失察深深自责。站在门口发呆,我的眼睛里吹进了一粒灰尘,揉揉眼角眼泪便流了出来。我轻轻敲了敲敞开着的老旧的木门。
左厢房里有人咳嗽了一声,我推门走了进去。昏暗的房间里我模糊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躺在床上。待适应了房间里的光线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脸色腊黄,形容枯槁,明显呈病态。他招呼我在病床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坐下,开始断断续续讲这个家庭的事情。
他是香香的父亲,已经清楚自己的病到了晚期。早先自己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一大家人生活基本过得去,这两年重病,花去一大笔钱,又没有了劳力,生活逐渐变得艰难。他说下午香香没去上课的缘由,肯定又是到乡下去挖草药去了。一个老中医告诉他需要这种草药做治他病的偏方。谈起香香的懂事和学习情况,他的眼神里闪动出少有的光泽,这个男人有着溢于言表的自豪感。过后,许是想到了什么,他的神色黯淡了下去,忧郁又爬上了他的眉梢。我安慰他,劝说他打起精神治病,等病好了带着这个家庭向前奔。男人咧嘴惨然一笑。我的心里一紧。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百元钱悄悄放在桌子上。在我告辞时男人眼里泪光闪动,转身走开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他用力说了一声:拜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