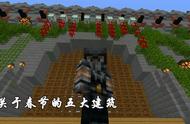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捉鱼
文/王明勇
【博士观点】中学生可以没有学术成就,可以形不成完整系统的学术思想,但不能不启发学术意识,不能不培树学术精神,不能不训练学术思维,不能不养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术习惯,更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话题缘起】2022年10月3日上午11:20分,王士弘给我发来两条*一是“石老人无了”;二是“被雷劈了”。
王士弘微信所称“石老人”,指的是一块早被赋予神话传说的屹立于青岛海边不远的,像似在翘首期盼亲人早日出海归来的站立老人形象石头。据说此石屹立于此已有6000余年的漫长历史,虽历经6000余年的风吹雨打,但外形没有任何改变,早已成为驴友打卡胜地和青岛地标性景点,久负盛名的“石老人海水浴场”即由此得名,起码是在青岛,“石老人”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块原以为风吹不倒、水侵不没的能够寄寓(jì yù,此处指寄托)一对新人“海枯石烂不变心”对天盟誓的海边石头的上半部分,竟然在2022年10月2日夜间或10月3日凌晨的颇有一些惊心动魄的风雨雷电交加之中,万分遗憾地永久灭失了。
【现身说法】关于“石老人”上半部分灭失导致形象毁损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甚嚣尘上且夹杂些许幸灾乐祸成分在内的说法,就是王士弘鹦鹉学舌一般微信推送给我的“被雷劈了”。毋庸置疑,在未见完整科学的鉴定报告之前,就主观臆断“被雷劈了”,既非学术态度,也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表达。对于一名涉世未深,价值观与审美标准尚未成型的中学生而言,如果允许其不假思索地像鹦鹉学舌那样以讹传讹 [yǐ é chuán é],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做的结果,与其他家庭、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教育可就真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那么应该怎样说,才符合学术规范和实事求是呢?在就这个话题与王士弘同学展开的对话讨论中,我对王士弘如此谆谆教诲[zhūn zhūn jiào huì]:“如果换作是我来向你传达‘石老人’上半部分意外灭失的消息,不管网络语言或者所谓的什么权威人士如何说法,我都会实事求是地如此叙述:据网传消息,据说已在青岛海边屹立长达数千年之久,已被赋予神话传说并已成为青岛人文骄傲的地标性景点‘石老人’的上半部分,在2022年10月2日夜间或10月3日凌晨的雷电交加与狂风暴雨中万分遗憾地消失不见了。”对我这个建议性表达方式,王士弘深以为然。
见王士弘同学对此话题讨论颇有兴趣,我就想趁机启发他的学术意识,借机培树其学术精神,让他养成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学术习惯,让其形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于是问他:“你能否告诉我耳熟能详的成语浑水摸鱼,为什么不是浑水捉鱼?或者说,浑水摸鱼与浑水捉鱼哪一个更加符合生活场景?如果两者都有出处或者分别符合不同的生活场景,为什么浑水摸鱼能被约定俗成为教科书的规范用语?”
毫无疑问,以上问题不仅出乎王士弘同学的意料之外,很显然也不是像他这样缺乏生活阅历的高二学生所能想象得到的逻辑范围。但这问题确实存在,以我的生活经验与切身体会而言,浑水摸鱼更加切合我曾服役一年多一点儿时间的浙江宁波一带的南方农村生活场景,而浑水捉鱼则更加真实贴切地描写了曾经生我养我的以我老家寿光王家老庄村为代表的北方求鱼方法。
具体而言,在我还是一个对周围一切都感觉新鲜,都充满好奇的少年儿童时代,我曾亲眼目睹老家寿光王家老庄村的许多次浑水捉鱼场景。在我印象中,浑水捉鱼的事情大多发生在炎炎夏日的中午饭后,已经下地劳累大半天的老少爷们儿,趁着午后日照正浓的休闲时光,相约一起拿着洗脸盆、洗菜盆等相对轻便的可以盛鱼工具,下到一个能与其他水流相对隔绝的大水湾里,有说有笑地一起脚蹬手刨地用力把水搅浑,为求步调一致,甚至有时还会有人兴致勃勃地喊起劳动号子(这种号子,在四到六个壮劳力协调一致地抡起沉重的石夯 [hāng],为村民盖房打地基的时候我也见过,场面极其壮观热烈,极有感染力,也极具震撼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浑水折腾,等到水湾泥浆泛起,河水不复清澈,水中的大小鱼儿,就会随着泥浆不断泛起而导致的水中氧气逐渐减少,一个又一个地陆续浮出水面,这时候,参与浑水的人们便眼疾手快地将其一个又一个地顺手捉入盆中,如此这般地持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抓鱼活动,往往既让已经消耗大半天的体力得到极大恢复,也让身体力行的浑水参与者随身自带的洗脸盆或洗菜盆中积累不少或大或小的种类繁多的鱼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样的缺衣少食的生活困苦年景,能有一顿满可以称得上丰盛的鱼虾来打牙祭,自然就是无与伦比的幸福快乐。
只可惜,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以后,那条蜿蜒流淌于王家老庄村东、老庄小学(原址在12公交车王家老庄村始发站附近,现如今早已不见小学校舍的一星半点儿影子,此处已被外村人承包后夷为停车场平地)围墙之西,曾经水草丰盛鱼游虾嬉的东跃龙河,竟然在不知不觉间自然干涸[gān hé]了,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这种浑水捉鱼的幸福热烈场景,我想,恐怕只有在这种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加真切理解体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实含义。
在我印象之中,浑水捉鱼的水湾之深,往往能够淹没到成年人的脖子上下。毫无疑问,在如此深水场合,期望以摸的方式来抓水中游鱼,既不可能,也不形象,必须将水事先搅浑,然后趁机抓鱼,这种语言环境下的抓鱼方法,自然应该叫做“浑水捉鱼”。
至于浑水摸鱼的场景,则是距离我在寿光老家东跃龙河边坐享其成于浑水捉鱼的十几年后,是我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某县的潜艇部队服役期间的一次外出购物期间的亲眼所见。那一天也是中午饭后,当我从隐匿在大山深处的潜艇修理厂踏着田间小路往镇上走,准备从镇上乘坐长途客车去县城购物的路上,突然远远地发现附近有个村庄,而村落附近的路边沟渠里有一大群人正有说有笑地弯腰探步往前移动,路边也有一些像我当年站在岸边欣赏浑水摸鱼的半大不小的看热闹孩子。已在大山深处的潜艇修理厂里憋闷许久,加之初到南方对一切都感觉新鲜好奇,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赶过去看个热闹的脚步。
赶到那里一看,才发现正在沟渠里弯腰探步往前进的这么一大帮子男女老少的人之所以移动速度这么慢,原来是在手拿小巧背篓一样的竹编工具和其它一些至今叫不上名字的用以抓鱼或者盛鱼虾之类东西的竹编器物,一边将其碗口样子的底部沿着脚尖儿前面不远的地方往水里扎压,一边弯腰用手在这器物底部接触渠底的周围探摸,而且时不时地有人摸出一条鱼把它扔进篓子里,基于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浑水捉鱼场景,我立马醒悟过来:原来他们这是在用跟我老家村民相类似的方式,在以集体力量协作抓鱼取乐呢。这路边沟渠的水不算太深,大概就是能够淹没到成年男人膝盖的样子,所以这群人也是大个子在中间,小个子分列两边,好像以人与人为节点织成了一张法力无边的网,不留缝隙地齐心协力弯腰探步往前赶,不言而喻,这张法力无边的人力大网经过之后,恐怕这条沟渠里能够侥幸逃脱的鱼儿不会太多。
与我老家的村民先把深水湾里的河水齐心协力搅浑之后再趁机把浮到水面上的鱼儿捉住不同,由于这里的沟渠水浅的缘故,他们是在一边缓慢向前移动,一边用手在水底探摸,当然,经过这么多人如此密集地探摸前行之后,沟渠里的水就不可能清澈,相应地,也会有被呛晕的鱼儿浮出水面,也就有人趁机抓住,但总起来讲,我所见过的南方这种抓鱼方法,相对而言更加配得上“浑水摸鱼”这个说法。看到这里,我禁不住哑然失笑,因为一个叫做“异曲同工”的成语突然之间几乎就要被我脱口而出。
以上两种抓鱼方法,尽管都是大家伙儿齐心协力地把水搅浑,但从表现形式上看,南方、北方还是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本质区别的,毕竟北方的“浑水捉鱼”,主要是抓那些浑水之后因氧气缺乏而不得不浮到水面之鱼,而南方的“浑水摸鱼”,则大多是在探摸那些潜藏水底之鱼,按照这个逻辑,在以宁波某县为代表的南方,就应该叫做“浑水摸鱼”,而以我老家寿光为代表的北方,就该叫做“浑水捉鱼”。但在华人语境的约定俗成里,尤其是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等汉语工具书中的规范表述,却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浑水摸鱼”。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以偏概全的“南方压倒北方”情况,由于我不是语言历史学家,对文字研究所下功夫也相对不多,所以除了可用“或许南方河网纵横,沟渠甚多,加之提到鱼米之乡就会给人平添无限向往,久而久之,吃鱼、抓鱼似乎就是南方专利,所以人们才会将南方的浑水摸鱼,约定俗成为汉语成语的规范表述”外,我真的不敢妄下其他论断。
对于我跟王士弘同学讨论研究的这个“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捉鱼”问题,很可能会被嗤之以鼻,因为这个问题看起来就是没事找事的吹毛求疵,对于早已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云亦云即可,再去探究为什么会“所以然”没有任何必要,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类似问题对于培养锻炼一个人的学术意识和思维习惯还是大有裨益[dà yǒu bì yì]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或者是在吹毛求疵。
在鲁迅先生笔下大作《狂人日记》中,我认为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一语中的地点出了芸芸众生既人云亦云也墨守成规的通病,那就是“狂人”反复诘问[jié wèn]的“从来如此便对吗?”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学术意识培养上,“狂人”反复诘问的 “从来如此便对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无独有偶,事关南方北方之争的典故,除了“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捉鱼”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发生在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政府与位于山西省汾阳县境内的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杏花村”商标之争。不言而喻,解决此类权属纠纷,需要比前述“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捉鱼”口舌之争更加细致入微地旁征博引。据说,全国各地有十多处杏花村,遍及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等八个省份,唐代大诗人杜牧《清明》诗中所谓“杏花村”究竟是在哪里?历来各地争论不休。
我想,即便杜牧先生能够活到今天,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想到他在《清明》诗中的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竟然在为后世留下一首千古绝唱,使得“杏花村”名满天下的同时,也会让人在“酒”与“村”之间引发一场持续时间长达七年之久的“杏花村”商标之争吧。
据互联网消息,直到2009年11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才在历时七年多时间,经过审核和复审两个阶段之后才算审理终结,通知核准安徽省池州市黄公酒泸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注册“杏花村”旅游服务类商标,并认为该核准注册不对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在先的“杏花村”酒商品类商标构成权利障碍。至此,这场历时七年之久的“杏花村”商标之争才算尘埃落定,而杜牧先生笔下的“杏花村”,也就因此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换句话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为酒是山西的酒,村是安徽的村。
据介绍,这个案子的审理不仅牵涉到人文,而且涉及地理,不仅需要论证南方司空见惯的水牛,与北方黄土高原上闻名遐迩的黄牛之品类貌相异同,需要从气象学上论证杜牧《清明》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实指江南初春景象,而非黄土高原上的山西汾阳状况,据说,安徽池州还以“自古以来在我国志苑中为村立志者,只有池州杏花村”为自己抗辩,很显然,办理这样的疑难复杂案件,如果没有“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捉鱼”一般的求真务实学术态度和吹毛求疵学术精神,必定难当大任。
回到王士弘同学人云亦云地向我转发“石老人无了”和“被雷劈了”之后,我为什么会如此周吴郑王和大费周章地批评他纠正他,就是因为我突然因此而意识到,我们当前的中学教育课程虽然很多,教学内容也已足够丰富,但唯独欠缺的,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学术习惯的鼓励养成和实事求是学术态度的培养坚持。
俗话说,一人感冒大家吃药。但愿我跟王士弘同学之间的这个有关“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捉鱼”的学习讨论,能够为中学生教育之启发学术意识和坚持学术操守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王明勇,男,山东寿光人,曾服现役30年,工学学士、军事学硕士、法学博士,资深律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曾任潜艇全训副艇长、海军北海舰队军事检察院正团职主诉检察官(四级高级检察官)、海军北海舰队法律服务中心主任,2016年12月退出现役后牵头创设山东水兵律师事务所并兼任律所主任、党支部*,2011年被中宣部、司法部表彰为“2006—2011年度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被解放军四总部表彰为“2006—2011年度全军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