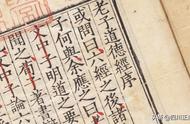作者:宋 羽
偶然读到白居易的《暮江吟》,竟被一句“可怜九月初三夜”感动到了,说不出什么原因,只觉得触碰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艺术“自留地”的边缘。
九月初三,不是节日,不是节气,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这个日子在白居易的诗里,似乎处于被忽视的位置——人们想象着“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致,回味着“露似珍珠月似弓”的灵动,甚至琢磨着“可怜”二字里透露出的爱怜、珍惜之情,至于“九月初三夜”,无足轻重的日子罢了,谁会在意它呢?
它偏偏几乎占据了整一行诗,以看似“无意义”的状态构成了一首七绝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暮江吟》是一幅画,那么“九月初三夜”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一片“无意义”的空白,为天地之间的山水留出了可供呼吸的空气,这种空白,就是物质与精神流动的空间,也是中国文人呼吸艺术气息的一片安静之地。
诗需要意犹未尽,画也需要余味无穷,而文字和笔墨未曾触及的地方,就是留白。
留白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渗透在传统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中的。镂空的花窗、镂空的回廊,连太湖石也一定要以瘦、漏、皱、透为美,在石头的空隙间感受光线和空气的流动。这是一种延续性的美,它让人的感官跳出了客观事物的束缚,进入了精神世界,进入了情感世界。留白,留下的是想象,而美,一旦进入想象的空间,就有了无限可能。
我相信古人对于时空的概念必有他们独到的理解,远近高低,既是诗歌,也是绘画和书法。看徐渭的写意花鸟,仿佛在看飘零的人生——墨葡萄在风中狂舞。风在哪里?风在留白处,这些飘忽不定的风,在葡萄的反衬下跃然于观者眼前。再看米芾、张旭的狂草,锋利的狼毫将怪诞狂妄铺陈开来,笔断意连,无墨之笔反倒更加变幻莫测,扣人心弦。
中国的文人自古就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们渴望坐看南山、采菊饮酒,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又舍不得“货与帝王家”带来的荣耀,他们读书、求学,满腹经纶只求考取一个功名。功名是什么?功名与理想无关,与诗无关,与人的存在价值无关,可它偏偏攫住了无数人的胳膊,让人挣扎不得。迫于生计,文人在他们的人生画卷上描绘了太多寻常人眼中“有意义”的图像,可越是如此,他们就越需要一些留白了,越需要在一些“无意义”的艺术形式里呼吸真性情的空气。于是九月初三的夜晚就成了永恒的艺术,成了无穷的遐想和怀念。
将留白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倪瓒。倪瓒的留白是为水域和天空准备的,他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山的轮廓,然后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白色,几乎不事墨色——将观者带进倪瓒的美学空间的,不是山,恰是水天处的空白。在倪瓒笔下,山只是陪衬,水和天才是主体,虚实和主次的关系在倪瓒的空间维度里发生了巨大反转。所以《渔庄秋霁图》也好,《秋亭嘉树图》也罢,倪瓒笔下的山水总透着点点寒意,大片的留白给即将南下的冷空气腾出了呼啸而过的空间——凉意在呼吸间浸透肺腑,最终化作无限的寂寞。
这样的意境,明代张岱在随笔《湖心亭看雪》中也有相似的表现:“雾凇沆砀,天与云,山与水,上下一白,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于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文学领域虚实和主次关系的反差,同样通过视觉上的留白手法来实现,不同的是,倪瓒的留白更为干净和彻底,他的画面是无人之境,是无我之境——他不是画中风景的参与者,甚至连旁观者的身份都不需要。
元末明初时代,山水画的构图还延续着宋元绘画的模式,尚未出现日后逐渐风靡的彩色长卷和册页。宋元山水遵循“三远”透视法则,即传统的高远、深远、平远,北宋后期的韩拙又提出了“阔远、幽远、迷远”的新概念,把山水创作从技术层面的构图法则推向了情感层面的氛围表现。
元人山水多用线皴,彰显点线美,看似弱化了具体事物的体积和造型,却通过线条的动感和墨色的变化凸显出空间的层次性,宏大的山水主题不再像北宋绘画那样压抑和密不透风,光线和空气,以及锋芒、力量和我行我素的潇洒在笔端恣意游走,这种形而上的笔法只有皴擦和飞白才能呈现。正如韦羲在《照夜白》一书中论述:“中国绘画美学的核心是书法美学,是云行,是水流,是花开,是树的生长……是作者的心性、品藻、风度、神智在时间变化之中的自然流露。”
倪瓒和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并称为“元四家”,他们在创作上讲究空隙和苍润之美,明朗通透的枯笔山水宣告了文人画标准画风的形成。回看整个元朝,东方传统文化和艺术几乎都处于一种自发生长的状态,像一片无人看管的原野,各种植物竞相生长,诗歌、散曲、话本小说、书法、绘画、杂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结出了不同形态的果实。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更愿意将目光投向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欧罗巴,他们醉心于马背上的征服,把江南留给了一群社会地位卑微却胸怀智慧和士大夫精神的文人。
这是儒家士大夫从庙堂走向乡野的时代,也是贵族气息、士大夫气息与平民气息相遇的时代,这是两宋画院里拥有官员身份的宫廷画师无法感受到的。有元一代,士人变成了文人,绘画中的匠气变成了文人气、书卷气,元朝统治者对文化艺术的漠视反而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
明代书法家祝允明说:“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意”成了古代画家们所推崇的新境界,吴门画派迅速发展壮大,文人画和院体画的鸿沟也随着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的出现逐渐消弭。从写形到写意,中国的文人画由此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心意和情绪成了绘画的灵魂,留白则成了艺术与性灵完美结合的表达。所以不管怎样,在广阔的、空荡的天地间,总少不了一座空无一人的亭屋。
空荡荡的亭屋,李成画过,米友仁画过,夏圭画过,王蒙画过,无一不传递出“充实”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逐渐扩展开来,扩展成了牧溪的柿子、郑思肖的兰草,以及朱耷的白眼孤鸟,最终定格成一个难以超越的标签。
其实绘画里的东西,诗歌里也有,你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白描,可偌大的画卷上还有大片留白,你想知道空白处到底是山上的风景还是山下的农家生活,可诗人却说“已忘言”,他说得那么洒脱又真挚,让你分不清他是真的忘却了,还是故意使性子不说。不说,反而比说了更让人心安。许多人生,因为“不说”变得简单和真挚了,就像许多诗歌,因为留白变得朴素和平易近人了。这样的人生和诗歌都让人感动。
好的艺术形式都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留下一些空白,喜怒哀乐就在这空白里。
空白是什么?是无限延伸的外延,是语言无法描摹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些空白,也是为了在下一次蓦然相遇时激起情感深处的波澜和感动。比如南朝陶弘景看山,说“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山上究竟有多少妙处?他也是只看在眼里,绝不说破——你若急切地想知道,何不亲自上山一见?
很多时候,人们感动于某种风景往往并非因其多么奇异,而是在那一瞬间与自己的情感碰撞出了火花。就像白居易所经历的那个九月初三的夜晚一样,他看到了残阳、江水、秋露、明月,这些景致并非九月初三所独有,在江南晴朗的秋日,你可以任选一天欣赏到江畔的落日和月光下的露珠。可是该需要怎样的情感上的共鸣,才能对这样的某个日子生发爱怜之心?美景常有,心意难求,正因为此,那一年九月初三的夜晚方显得这般珍贵,珍贵到需要用诗的方式来铭记它的不朽,需要用画的留白来供养它的生命。
想起已故作家汪曾祺说过的一句话:“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从未着墨色的空白之处,我似乎看到别有情怀的人文艺术。(作者为艺评人)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