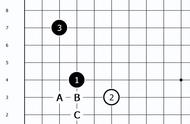陇东方言形容词:希忽儿、秀柳、兮兮儿的、霍霍儿的……
秦玉龙/文

曹臧恰我哩俺的陇东平凉人,用本土话形容一个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为“斜抽马侉”或“窄楞仰拌”。所谓“斜抽马侉”,意为“不正”。追根溯源,“马”是“码”的别字,指样子、样码。“侉”意为“虚空”。“人”与“夸”联合起来表示“浮夸之人”“华而不实之人”。侉字本义:举止夸张,言谈怪异的人。
窄楞仰拌,也写作仄楞仰般,形容某人倾斜着仰面跌倒或躺倒。意为说话做事不着调,不按路数来,与斜抽马侉意思相近。
其实,陇东方言中有很多形容词,因为是记音口头语,字词之间少有关联,组词没有明确寓意,不熟悉当地方言的人,很难从字面上理解它要表达的意思。
如常用的麻眼、蛮的、秀柳、蔫哩苦出、背不咋、光把连西、硬头骨抓、烧料子、忙辈、眼隙稠、日乎朝天、洋气的、油干眼子尽、罢咧、麻达、颇烦、捏过、短死鬼、毕蹬了、干散、零干、猴的、立马玄天、克里马嚓、希忽儿、兮兮的了、乱麻失眼、毛鬼神、驴死鞍子烂、日肚来嗨、扑次来嗨、细数、莫交先、淡么、肘的很、胡倨冒撂、啬皮、撅沟子、松沟子、二杆子、瘦狗鼻子尖、心黑叶子麻、品麻、然怂、楞怂、增怂、犟怂、碎怂、攒劲、孱活、松泛、花泛、活泛、窄恰、日眼、丧眼、庆皮、三锤两梆子、年窝、倭也、受活、美日塌咧、不卯、离皮子、嚯嚯儿的、你个货、增三、哈米失眼、死狗烂娃等等。

探究方言词语的意义,必须找到它的语源,即方言词语的来源。语言学家认为,方言的来源一般有三个:一是古代流传,二是当代创造,三是外面传来。然而,一般之外还有二般三般,方言在长期流传使用过程中,因为地域不同,发音不同,使用者文化素养不一,导致方言出现变音变字,结果这一变,变得面目全非,变得六亲不认,也就找不到它的源头和出处了。
以陇东渭州方言形容词为例,我们常说的“麻眼”,形容人和事物比较麻烦或难办。“麻”是“码”的谐音,“眼”是“蔫”的谐音。“蔫”意为精神不振、性子慢、不爽快。“码蔫”,持续地萎靡不振。然而,在陇东方言中,“码蔫”从字到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异,“麻眼”既形容事情棘手难办,也形容某人眼神不好或识人看事不清,如常用语“日麻眼”。
秀柳,语源是以婀娜多姿的垂柳形容女人身材苗条、窈窕、细长柔美之意。在一些方志中,“秀柳”写作“秀溜”,“溜”是“柳”的别字。
忙辈,烦躁之意。查方言典籍,“辈”是“迫”的别字。平凉话“辈”和“迫”发音相近,如把“压迫”读作“压pei”。迫,压制、紧逼,急迫、迫切,迫不及待。所以,“忙辈”的正确写法应该是“忙迫”。

油干眼子尽,语源是以油灯燃尽来形容精力或钱财耗尽。这里的“油”是指清油或煤油灯用的油。“眼”是“捻”的别字。“捻子”是油灯点火用的棉线,也叫灯芯。
毕蹬咧,完蛋、结束之意。语源来自古汉语引申语义。毕,完毕、结束。蹬,蹬腿儿了,形容某人生命到了尽头。 希忽儿,差一点、很危险,幸免灾祸。如:刚才希忽儿就碰到车上咧。语源很有可能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变异。
兮兮的了,形容坚持不住了,让人讨厌至极,受不了了。语源出自古汉语,“兮兮”是“细细”的别字。细,微也,最后一丝力气。
毛鬼神,形容某人毛手毛脚,鬼鬼祟祟,神神叨叨。语源有可能来自古汉语。“毛”恐惧、惊慌。例句:心里发毛,害怕、惊慌。平凉方言“毛鬼神”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害怕鬼神,而是比喻其不稳重或举止失当。
驴死鞍子烂,形容事物一塌糊涂,无法收拾。语源估计来自百姓日常俗语,驴死了,鞍子烂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淡么,稍微、些许之意。例如:你没吃饱吧,就淡么咧一下。淡,轻描淡写。么,细小。“淡么”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浅尝辄止”,意为略微尝试一下就停下来,指不深入钻研。

肘的很,形容待人傲慢,架子大。《西安方言词典》释义:自以为比别人强,看不起人。与“胡倨”意思相近。
瘦狗鼻子尖,形容某人嗅觉灵敏。语源来自日常俗语。瘦狗,在平凉方言语境里不单指狗很瘦,而是一种比喻戏谑之词。
蔫哩苦出,形容一个人无精打采、萎靡不振。陇东学院教授刘瑞民认为,“苦出”是“枯搐”的别字。枯,枯萎。搐,收缩。
不卯,不合卯,形容人与人的关系不和有矛盾。卯,榫卯。
霍霍儿的,轻轻的,形容某件东西要轻拿轻放,或代指某个事物必须轻轻去做,不能动作过于猛烈。如:我手疼的,你霍霍儿的摸一下。
三锤两梆子,也写作“三槌两棒子”,形容做事快速麻利,两三下就完成了。语源有可能来自铁匠打铁或古人报时敲梆子,也有可能来自与捶打有关的农活。有些地方志书释义为“干干脆脆”,有些解释为“几句话将事情办成”或“做事敏捷”。
陇东方言中的形容词,是当地百姓日常生活的口语,语源出处或许不同,县区之间也略有差异,但它的生动有趣,诙谐幽默,极大丰富了平凉方言内涵和表达方式,既高雅又通俗,既豪迈又婉约,既直白又深奥,是陇原方言大家庭里不可或缺的宝贵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