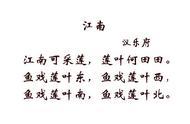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所谓“救亡”,是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随时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中国现代史的重大主题。
所谓“启蒙”是说,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需要引入,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的政治体制需要建立,人的现代化是“启蒙”的核心内容。
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1926-2010)的研究,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9%,这一优势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超过。
麦迪森的数据测算存在一些争议,但即使将这些争议考虑在内,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在西方与中国交手的头半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一个经济强国。
然而,这样一个经济强国为何总是败于列强之手呢?原因在于,中国的军事不行,国富而兵不强。兵不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军事制度落后,另一个则是军事技术落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马上意识到了后者,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体系。
所以,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林则徐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谈到西人之所以战胜的原因是兵器先进:“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之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国图志》,书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正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且把夷之长技规定为“船坚炮利”以及军队建设管理之技。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着全部近现代史。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
而所谓落后,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对军事技术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中国人的强国梦和潜意识。
对航母、对宇宙飞船的渴望,几乎是今天的全民共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屈辱,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现代科技体系推崇有加。
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会不由自主地使用“科技”一词,而他们口中的“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
政府也一样。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如果做一个民众认知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人所认可的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爬梳古文献或许偶尔会遇见“科学”字样,但意思一定是“科举之学”,而且极为罕见。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日本文字中大量采用汉字,但发音与汉语不同,意思也相去甚远。中国现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原因大致有三。一来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立即直接译成中文出版发行。
传统中国对文字过于讲究,虽然有西来的传教士,但他们的中文写作水平还不足以独自担当翻译工作,所以,西学东渐早期的西方著作翻译都是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进行,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西文著作的汉译规模和进度。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较早,而且日语吸收外来语的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动作迅速且规模大,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现代中国人多经由日本向西方学习。
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阅读日本文献非常容易,哪怕是根本不懂日文的人,读日本的书也能明白个大概。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船上读到一本日本小说,发现居然满纸汉字,也知道其意思不会差太多,于是在基本不通日文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日本小说。
说是翻译,其实只不过是把日本人采用的汉字基本照搬过来而已。就这样,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向日本学习西学的热潮。
的确,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上手容易,见效快。大量向日本学习的后果是,现代汉语受到日语的巨大影响,一大批西方学术术语均从日本转道而来。有人甚至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有70%来自日本。
这些术语充斥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一定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日本这个民族在文化底蕴和思维深度方面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现代中国的文化以这样大的规模和强度建基于日本文化,实在值得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一再反思。
已经有不少人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学科的译名存在的缺陷。比如,用“哲学”译西文的philosophia,没有译出西文“爱”(philo)“智慧”(sophia)的意思来,相反,“哲”是“聪明”,“哲学”实则是“聪明之学”,这降低了西文philosophia的高度。
如果选一个更合适的词,也许“大学”更接近philosophia的高度和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颇有西人“爱”智慧的意思。

严复当年就对大量采用日译词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均着眼于日译词汇完全偏离了汉语本来的意思。
他反对把economics译成“经济”,主张译成“计学”,因为“经济”本来是“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而economics只是指理财经商,把原来的语义缩小了;他反对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主张译成“群”,反对把sociology译成“社会学”而主张译成“群学”,因为“社会”本来是“乡村社区祭神集会”的意思,而society意思要更加广泛和抽象;他还反对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主张译成“理学”,反对把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主张译成“玄学”,反对把evolution译成“进化”,主张译成“天演”。但很可惜,这些更为精到和地道的严译术语最后都遭到了否弃。
让我们回到“科学”。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诸如naturalphilosophy、physics等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起见,译成“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
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课,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读,认为它是指“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用中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太深的中国印记,而且也容易混淆。
20世纪头二十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种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种是音译。
五四时期流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音译,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译“德谟克拉西”,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的音译“赛因思”。最后淘汰的结果,日译名词大获全胜。
今日的科学、民主、自由、哲学、形而上学、技术、自然等词全都采纳了日译。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次出现在中文文献之中。
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杜亚泉,他于1900年创办并主编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开始就成为science的定译。
另外,严复在1900年之后也开始用“科学”来译science,影响自然非常显著。20世纪头十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
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1886-1961)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
1959年中国科学社被迫解散,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于次年停刊。1985《科学》杂志复刊,今天仍然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和白春礼院士先后任主编。把science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本义,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学”的是另一个词discipline(学科)。
不过,日本人倒是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就是,自19世纪前叶开始,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始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反观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学问,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不分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用“科学”这种区分度比较高的术语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显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
我们的“中国科学院”并不叫“中国自然科学院”,相反,其他的科学院则要加限定词,如“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等。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人文学科分手、并且愈行愈远最终走向“两种文化”的实情。
这样一来,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指自然科学。如果加上前述的“夷之长技”,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还可以加上第三条: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
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观念只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不是“本”,要由这个“末”回溯到西方科学之“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本书余下几章就要做这个工作。

前面提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救亡运动中,科学作为“夷之长技”被引进,被尊崇。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则进一步上升为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只有认识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才能理解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何以某个人群(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科学)能够直接作为正面价值判断的术语。
一部现代西学东渐史,也是一部科学由“技”转化为“道”、由“用”转化为“体”的历史。即使在急迫的救亡时期,要想大规模地引进科学这种“夷之长技”,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科学这种本质上属于外来文化的东西,与本地文化实则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术贬称为“奇技淫巧”。
所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理论基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说,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社会制度,同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富国强兵,解决民生问题。
或者说精神文明取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取西方现代的。又或者说,中学主内,西学主外;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但是,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光是学习军事技术是不够的,也学不好,必须首先学习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等在内的西方科学理论;要想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掌握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必然会挑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洋务运动近四十年中,上述逻辑充分发挥了作用。等到1895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洋务运动宣告*之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传统,都需要来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这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痛恨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文化虚无主义逐渐笼罩中国的思想界。这个时候,“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要代替从前的“中体西用”。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在核心位置。
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指的则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另一方面开始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的理论体系。
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新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但他们偏偏都把他们并不熟悉的“科学”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何以故?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全盘*之后,留下一个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作为替代。科学作为西学中国人最为钦佩也相对最容易接受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
这里当然也还有中国传统的“致用”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与西学中的其他东西比起来,科学似乎是最能解决问题的。胡适说过:“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科学脱离了具体的研究事业,上升为一种信仰,从此,作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
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与人生观》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是当年那场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历史上也称为“科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
这场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确立。实际上,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就已经十分鲜明和突出。
在新学与旧学、文化开明派与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与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了前者当然的旗帜。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这样热情讴歌科学,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
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思想领袖胡适,尽管与陈独秀政治观点大不相同,也高举科学之大旗:“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大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读中国古籍。他说:“我也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相互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科学的学庸》)
*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看到,不论政治立场有何不同,不论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们都把科学默认为好东西。这就是当代汉语里“科学”一词第二种用法的历史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