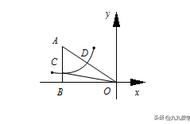竹林七贤聚饮时,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我行我素。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应付环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最后结局也不一样。

他们生活的时代,基本是曹魏政权开始受到司马家族威胁并面临改朝换代的时期。七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嵇康,他打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号,公开蔑视礼教,鄙薄世俗,毫无顾忌,胆识惊人,名士都以与他同游为幸,视他为“精神领袖”,同时也是司马氏极力拉拢的对象。
嵇康是一个正直的学者,痛恨司马氏的倒行逆施;他又是魏室的姻亲,在感情上同情曹魏皇室。痛苦彷徨之际,他模仿屈原《卜居》,写了一篇《卜疑》,借虚拟的宏达先生之口提出疑问:我是宁可竭尽忠诚在朝廷秉正执言,绝不屈服于王公权贵呢?还是小心翼翼地秉承旨意、胆怯地顺从呢?是宁可斥责驱逐凶恶邪曲之人、始终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呢?还是欺世玩世、用尽心机、为他人出歪主意呢?是宁可隐藏鳞片的光彩,像蛟龙潜于深渊一样?还是高飞长鸣、像云中的鸿鹄那样呢?……诸如此类的多个问题,其核心内容便是仕与隐的问题。嵇康之问,也是其他士人面临的问题。
刘伶有过几次短暂的入朝和参军经历,但他仍然维持着邋遢作风,后来晋武帝司马炎把他召去策问,他仍然坚持宣扬无为而治,与皇帝对着干,结果被赶走。刘伶在酒坛里度过余生,保留了在竹林时期的气节。
阮籍寄情山水,不问世事。司马氏为了拉拢阮籍,想和他结亲,阮籍大醉60天,让提媒的人没有机会说话。司马炎篡位时,把写劝进表的任务交给阮籍。司马炎派人去取时,却发现他趴在案上醉了,什么都没有写,于是把他摇醒,让他在醉中强行写一篇。阮籍只好完成任务。
不与司马氏合作,结果被构陷*害的嵇康死后,作为嵇康密友的向秀也成了目标。为了避开司马氏的迫害,他不得已应诏担任了一些闲职。但他选择了做官不做事,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度过了危机,也保留了自己的气节。
阮籍的侄子阮咸,生性放达,无拘无束。虽然挂着官职,实际上却远离官场,过着自己的日子。他钻研音乐,完全不去考虑官场的钩心斗角,只做自己喜欢之事。
山涛虽然也读老庄,并不反对出仕。当初弃官,更多是出于自保,避开司马氏与曹爽的争斗。一旦司马氏确定胜利,山涛意识到必须投靠他们,就再次进入官场。山涛能够识人,向朝廷进荐了大量人才。最后山涛官至司徒,安然善终。死时家无余财,是士大夫的榜样。
官瘾最大的是王戎,是七贤中的异类。他年轻时乐于参与竹林宴游,随着司马氏得势,他很快就奔赴官场。他位至司徒,晋身最高官员行列。他有很强的私心,是个财迷,购置了大量田产。后因派系之争而失去官位,又因战乱而颠沛流离,死于逃亡途中。
从他们七人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看,大体上可以如此排序:王戎、山涛、阮咸、向秀、阮籍、刘伶、嵇康,越往后排斥政治的思想越强烈。嵇康天性难驯,反抗激烈;刘伶倔犟强硬,不肯低头;阮籍心有原则,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避祸;阮咸疏离政治,自娱自乐;山涛借势出仕,以建功业;王戎依附权力,谋取富贵。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竹林”不大,却尽现士人之态。一直以来,这个群体被当作蔑视强权、追寻自由的精神象征,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士人面对政治和权力时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