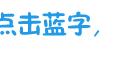儿时的一首童谣,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时时令人回味,窃笑。它以“人之初”开头。
《三字经》云: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但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却是变调走样的。我小时候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人之初,搬马杌。性本善,越打老爷越不念。老爷才到念会了,一打打成个糊涂蛋。”
显然,这是淘气孩子对《三字经》的亵渎,恶搞,篡改。这种篡改,以一种更加符合孩子们口吻的顺口溜形式,在孩子们中广为流传。似乎孩子们对这种个别人的“恶搞”不仅不反感,反而兴趣大增,传而诵之,传而播之,“流毒”甚广。
这是河南版的“恶搞”。在山东临沂也有类似的恶搞:
—- “人之初,盖小屋。盖不上,急得哭。”
—- “人之初,出门站。新兴近,向城远。”
这里,“新兴”和“向城”都是地名。大概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临沂附近吧?
河南版的《人之初》中,马杌,是凳子,四条腿的木头凳子,又叫杌子。“去,给爷爷搬个马杌放院里。”小时候爷爷常常让我搬马杌。
在这首以“人之初”起头的童谣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是,孩子在私塾受到了先生的责打,从而产生了抵触和厌学情绪—- “越打老爷越不念”,刚要念会时,先生偏偏举起了手板,结果呢,“一打打成个糊涂蛋。”打骂,体罚,是先生的无能,其结果往往是实得其反,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挫伤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于是,童谣成了控诉状。它只能背后控诉,不敢当面直言。
浇灭一个孩子的学习兴趣易,培养一个孩子的进取心难。
山东版的那首童谣中,“出门站”意味着学生离开了教室;“急得哭”则是宣泄肚子里的委屈。
两首童谣,彰显出豫鲁两省孩子的创造力。他们将原版《三字经》“翻唱”成为花样百出、格调别致、酣畅淋漓、童心满满的新童谣。从“翻唱”这个角度看,它们应是当代歌曲翻唱的鼻祖或先驱。
翻唱也罢,并无恶意的“恶搞”也罢,孩子们似乎特别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创作”。凡是正版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修正,去翻唱,去恶搞,使之成为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古代有,近代有,现在也有。例如,大作家王蒙收集的幼儿园恶搞版的童谣就有一二首可供展示:
— “爱跟不跟,板兰根。”
— “一个小孩儿写大字,写、写、写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火啦,火、火、火车头,打你一个大背儿头。”
这两首儿歌,展示了孩子的非凡才能和想象力。
第一首,“爱跟不跟”,你不跟我玩也没什么,但你要小心“板兰根”!从“跟”跳跃到“根”,进而联想到板兰根,将他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药,一下子抛了出来,这种跳跃式联想,大跨度的灵机一动,恐怕非成年人所能为。
第二首,釆用了顶针续麻即首尾相连的手法。它一气呵成,海阔天空,由写大字到火车头,最后以“打你一个大背儿头”喜气洋洋地结尾,俏皮,搞笑,胜利凯旋,还占了个小便宜。
这使人联想起评剧《花为媒 》中的洞房张五可与李月娥的那一大段唱,顶针续麻,妙语连珠,令戏迷大呼过瘾。编剧吴祖光的文釆大放异彩,使该剧久演不衰。
经久不衰的对经典的嘲讽式儿童“恶搞”、翻唱,在笑声中令人回眸原版、正版,从而由侧面看到正面,迂回性地记住了正版、原版。作为教师的我,觉得孩子们创造了另类记忆术。这种记忆术的特点是,以熟推生,以歪记正,以活泼勾起严肃。这类童谣实在可爱,可珍,可敬可佩,可赞美,决不应挨打挨骂挨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