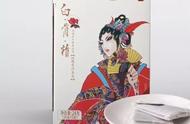钧窑,位于河南省禹州市,是北宋晚期宫廷秉承徽宗意旨,专门设立制作皇家用瓷的官窑。因窑址与夏朝王室(夏启)诏令诸侯会盟祭坛“钧台”毗邻,故名钧窑。钧窑,以青釉为宗,窑变为饰,久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美誉。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之分;窑变有海棠红、玫瑰红、葡萄紫、鸡血红等若干品种。因工艺要求极高、火控难度极大,成品概率奇低,成功之作“万里挑一、千金难求”。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宁要钧瓷一片、不要家产万贯”之说。钧窑制作可上溯到盛唐,河南鲁山窑以黑釉窑变著称于世,赢得钧窑“开山鼻祖”之誉。宋代皇室崇尚道教,推行“无为而治”。天青,是道家图腾至高境界,“爱屋及乌”的互动效应,直接影响到瓷器釉色定位和艺术审美走向。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均以青釉为本。但就制作工艺、审美标准、文化内涵而言,宋代青釉已远迈隋唐。主要标志: 1.越窑胎质粗放,形制粗犷;宋瓷胎骨缜密,烧结坚致。2.越窑釉质晶莹,有玻璃质感;宋瓷釉质乳浊,温润'如玉。3.越窑釉层稀薄,青中泛黄;宋瓷釉质丰腴,青中透蓝。4.越窑定位草根阶层,以日常用品为主;宋瓷隶属皇家用瓷,以仿古为重。宋代瓷业扶摇直上,离不开五代秘色瓷推波助澜。秘色瓷,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风靡天下。周世宗(柴荣)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那般颜色作将来。” 为秘色釉确立了最具权威意义的审美标准和文化内涵。也为宋代青釉厚积薄发,奠定了不可小觑的认知基础和创新理念。


启始于宣和年间的钧窑,是北宋皇室继汝窑之后设立的第二座官方窑口。宋徽宗迷恋道教、尊奉黄老、荒废朝政、玩物丧志,是声名狼藉“亡国之君”,政治上昏聩无能、治国无方;艺术上才华横溢、造诣精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鞠僦斗茶”无一不通。审美层次独领风*,文化底蕴傲视天下。他对艺术的执着,瓷业的痴迷,促使釉下高温瓷,打破单色釉传统束缚,开创出窑变钧瓷“色彩丰富、奇幻无穷得意之作。把宋代“瓷韵之美”推向极致。据明初吕震《宣德彝鼎谱》记载:“内库所藏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又据清代许之蘅《饮流斋说瓷》评述:“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 这些,足以印证宋代钧窑历史存在、弥足珍贵。上述月白釉蒜头腹花口樽是北宋钧窑典型制式。蒜头花口觚,是北宋仿商周青铜器高端器型。此器,高16.6厘米,最大口径14.5厘米,足径11.6厘米。胎质灰褐,坚固缜密。胎体敦厚,形制高古,典雅庄重,气韵贯通。蒜头腹,花瓣口,粗长颈,唇口圈足,足际平切,中规中矩。腹部,六瓣蒜头,同心连体,抱团相聚,均衡布局。六出弧线,自下而上,由细而粗,依次延伸,六出花口,塑形逼真,状似盛开的牵牛花,又名“喇叭花”。整体造型雄健壮硕、气宇轩昂。洋溢一派“气吞山河、舍我其谁”的王者风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十足霸气。将春秋战国“群雄称霸、逐鹿中原”的英雄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叹为观止。蒜头腹花口樽,上古社会,是王室置顶礼器,帝制社会,是皇家祭祀标配。北宋立国之初,摈弃盛唐奢侈铺张之风,张扬以俭入廉正气。珍惜商周古器、以瓷质制品替代青铜礼器,力促瓷器制作开布新局。此器,内外通施素雅华贵的月白釉。釉质丰腴,温润肥腻,釉表酥滑,抚之如玉。渗透出光怪陆离、垂涎欲滴的紫红色窑变。钧窑紫色窑变,基于道教图腾潜移默化。据司马迁《史记 老子传》记述,西周末年,诸侯割据,天下大乱。老子弃官归隐,途径函谷关。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东来,老子果乘青牛而至也”。尹喜热情款待。老子感其心诚,小住数日,“留下六千言《道德经》,骑青牛西行而去。* 这也是道教“尚紫”的由来。宋徽宗创立钧窑,以紫色窑变开宗立派,是一代帝王崇尚道教的一大佐证。此器,紫红色窑变若隐若现,与云遮雾障的月白釉,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传达出幻化神奇的审美情趣,含蓄内敛的艺术美感。“酒喝微醉、花看半开”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艺术表达,让人不禁想起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御窑工匠追求尽善尽美的良苦用心,让人惊羡不已。釉面通体开片、片纹稀疏,纵横交织,结体自然。足际裸露,垫烧痕、石英砂历历在目。外底,紫红色窑变深沉靓丽,行迹怪异的“蚯蚓走泥纹”杂以其间。此藏品,形制古拙,釉色精美,窑变神奇,意蕴丰厚。渗透着道家返璞归真的终极目标,顺其自然的价值理念。是北宋钧窑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精细之作。

宋代重文轻武,实施“文人政治”,使军事实力日渐衰弱。公元976年,赵匡胤“驾鹤西去”。靠“烛影斧声、逆袭上位”的赵光义“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征服北汉之后,不听群臣劝阻,以疲劳之师,兵指辽地,以期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酿成“折戟沉沙、一败涂地”的悲催结局。北宋元气大伤,颜面扫地。辽军“得陇望蜀,屡犯中原,劫掠众生”。面对蛮族金戈铁马,宋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真宗不得不“割地赔款”,换取一时休养生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息兵,北宋迎来相对安定的百年发展机遇。北宋中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国库丰盈。但,山河破碎,疆域缩水,始终是萦绕时人心头的黑色阴影。加上文人膨胀、“三教合一”影响,宋人生活方式、审美模式,渐次从唐代“富丽堂皇、热烈奔放”,转化为“含蓄内敛、小家碧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雨过天睛云破处”的青瓷之美,或许能给人带来带来一丝暂时的澄澈、清静和慰藉。这也是宋代青瓷名噪一时的社会基因。北宋官窑、汝窑青釉,倍受皇家青睐、达官膜拜。徽宗时,受道教文化浸润,以青釉窑变为主打品牌的钧瓷横空出世。一代帝王赵佶亲自主持编撰《宣和博古图》,把仿商周礼器作为皇家用瓷首选。瓷器,是火与土的艺术。特定历史宏观驱动,加持钧窑艺术底蕴、文化底蕴,远迈道教文化。它所蕴含的“抗争意识、民族气节、爱国情怀”,植根炎黄子孙血脉,生生不息、世代传承。“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靖康之难”以后,江山易主、京都南迁。钧瓷失去皇家垄断,流入乡村市井。构成乡绅富贾、草根阶层日常消费之器。不仅河南量产巨大,并波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内蒙、广东等,众多省份和地区,直到元末明初,仍风行天下、势头不减。显现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生存空间。这也是钧瓷文化与华夏一脉相承的明证。上述藏品,形制高古,釉色妙曼,装饰神奇,意境高远。釉表酥光内蕴的膜状包浆,釉层,参差错落的自然开片、釉下色调紫黑的老化气泡,乃至,足际特征鲜明的垫烧痕,石英砂,以及通体流露的当属北宋官钧妙不可言的熟旧感,都是北宋钧窑历经沧桑的客观折射和真实反映。
题目:《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
副题:宋钧窑月白釉蒜头腹花觚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