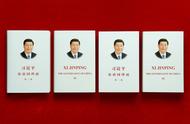海明威 画像
对于消解“死亡”恐惧的办法,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选择了塑造“硬汉”人物形象来克服。纵观海明威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具有阳刚特征的男性,分别以斗牛士、士兵、拳击手、猎人和渔夫等身份出现。他们缺乏文人的优雅,也不太讲文明社会里的礼仪,面临困境时,都趋向于一味的去拼、去干、去死。这些“硬汉”在他的笔下,经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创伤,身心备受煎熬,同时又赋予他们强大的力量和刚毅的品质,使他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体现出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硬汉”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传递了“正能量”,同时鼓励读者敢于直面人生的惨淡,勇于挑战人生的极限。海明威的策略是成功的,他的作品,包括他自己都曾被美国社会视为精神领袖,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
海明威本人也在“硬汉”形象的影响之下受益良多,填补了他早期经历中对于“死亡”情结的创伤,实现了自我治疗。在他的人生中,将创作与创伤用“硬汉”搭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他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
战争在海明威的人生中和作品中都不是陌生客,可以说他的作品几乎是伴随着他人生中的参战史成长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想加入海军陆战队,但是由于视力问题而被淘汰,之后他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当了一名司机。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收集在军工厂爆炸中丧生的工人尸体残骸。这段经历在他的作品《死人的自然史》中重现。

一战中的海明威与护士们在一起
他是一个冒险家,在战争中一直渴望到最前线,当机会来临时,他从不放过。1918年7月8日,当他将物资运送到驻扎在河岸的部队时,遭遇了奥地利迫击炮的袭击,弹片四处飞溅,耳边是一阵机关枪的持续射击声。在他的回忆中,他说他感到自己的肉身从躯壳中急速的飞出,他以为自己死了,飘浮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又感觉自己滑回了躯壳里,总算捡回了一条命。这次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全身约227处穿孔,他不得不花费六个月的时间来修补自己的身体。这段经历在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也经历了类似的场面。海明威在经历这一切时,也不过是个19岁的孩子。
此后,他的创作逐步开始涉猎战争题材,在随笔《在我们的时代里》,海明威在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机械化战斗和错综复杂的联盟中所特有的暴力和非人格性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是一个带有战争创伤的青年,在意大利驾驶飞机时他失去了命根子,他自叹“这真是一个烂透了的伤”,杰克的伤口代表着战争无形而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中,涉猎了战争和爱情两类题材,男主人公亨利的遭遇几乎与海明威在一战的创伤如出一辙。美国救护车司机亨利与护士凯瑟琳相恋,通过他们的爱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在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对人的精神和情感上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非洲狩猎中的 海明威
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四次奔赴西班牙,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热切的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他的剧本《第五纵队》和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都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仍旧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对各大战事进行报道。战地记者是非战斗人员,他们都肩负上尉的荣誉军衔,但被禁止携带武器或命令部队。但对于爱冒险的海明威来说,他还是冒着被处罚的风险参与到了一起情报活动中,为此,他受到了调查,所幸没有被定罪。
战争中的人类不可避免的触及到“死亡”,而要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中生存,唯一的出路便是奋起抗争,与自己斗争,与环境斗争,与敌人斗争,不顾一切的去捍卫自己的生命和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形象可以说是在战争的洗礼中被迫走向了不自觉的抗争。

海明威作为一个拥有不平凡人生经历的现实中人,他喜欢媒体把现实生活中的他,塑造和宣传成如他作品中类似的硬汉形象,他特别喜欢别人称他为“老爹”。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绰号,他努力在他感兴趣的领域成为专家,然后带着家长式的权威,把这些知识传递给他作品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他的小说里变成了英雄,成为各项技能的持有者,比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斗牛迷杰克首屈一指,《丧钟为谁而鸣》中炸桥的乔丹,还有最著名的捕鱼能手《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
他的一生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用他的作品,用他的一些不寻常的行动,不断的进行自我维护。不论在他的作品中还是他本人,都习惯摆出一副优雅的风度来应战,都找到了一种现代生存方式,即硬汉子生存方式。他认为,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斗争,而人在这场斗争中永远不可能取胜,人生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被说明、被改善或被拯救,死亡永远是一个定式而且不可选择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