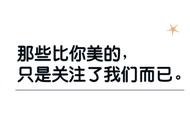苟活系列——狼口余生
孙国辉
晚八点,我们的大货车开进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乌拉一个大车店。司机赵永利和我又饿又累,冻得噤噤(瑟缩)着……店伙疤痢眼㨄着棉门帘子让我们进屋,倒上滚烫的奶茶让我们暖和着,回手麻利地烧水炒菜,一边犯了“话痨”(说个没完):
“那啥,还是林西吃的饭吧?肚子没食更冷,先吃两块热乎把肉(手把肉),……来喽,这是牛肉炒辣椒皮,也没啥青菜……那啥,烫窜的‘牛逼散’(白酒)来啦!给二位满上喝着,我再炒个土豆丝儿……”
我和永利呛(吃)了几块把肉,打住心慌(饿)之后端起了酒杯,顿时身上暖了起来。

“那啥,十来天没来车了,你们这是头一辆,道上难走吧?来,这是氽羊肉,趁热喝两口。咋着,‘眼镜子’,这酒你喝的是真‘尿’呀,‘咕咚咕咚’的(暗含调侃)……你们俩胆子不小,这天敢跑单车,活腻歪了吧?”
“老疤痢眼子,你这臭嘴逼咂个啥?呆会儿把车上几袋子煤卸下去。别整菜了,上炕跟爷们划几拳,看爷们儿咋瘦(收)拾你……”
“哟!‘眼镜子’,你红了毛了啊!上回我赢你不开壶你忘了?瘦马干哧的你个揍相!我告诉你,夏天你来让我们营子老*娘们把你拽庙后(指背人的地方)去祸祸死你……那啥,来着:‘锅(哥)俩好好啊!七枚巧啊,六大六顺’”……
二斤高度散白酒喝下去了,一致同意喝着“遥山橹”(用来代茶的植物叶子)哨(聊)会儿。
“那啥,咱说诊(真)格地,这天跑车太险了,住下吧。等来了车打伙走,也压开道了。‘眼镜子’你忘了前年冬天咱俩上林西,也下大雪,半道上看着那个冻死的开车师傅把大厢板儿和轮胎都烧了,死尸坐地上,眉开眼笑的,伸手烤火的架势,看雪都是火……冻死的人都这样,我看了好几个了……那啥,万一有个闪失,咱单车不担沉重……”
我恼了。
“闭上你臭老鸹嘴!我告诉你疤痢眼子,现今也下大雪,爷们儿哥儿俩天生福相,趋吉避凶!你说住下,爷们偏不住!明个起早走!*别在这饽饽(瞎说)了,去!给爷们儿烧点水烫脚!”
酒喝得不乐和,我和永利为了暖和及不着虱子,脱光腚背靠背钻一个被窝里。暗忖老疤说得对呀!天寒雪深,前车有鉴,老疤是一片好心哪!一定得加小心……太睏,先睡再说……
天刚亮永利就起来了,驾(用)喷灯烤车的吸气管子。我和老疤忙着烧水往水箱和机器里加水。捂盖(鼓捣)了半天,车打着了(发动机启动)。老疤不知道我从部队汽车连借来了喷灯,早早弄了一大铁撮子炭火在车下烘着闸箱、油底和后桥(差速器),更加快了低温下发动机的启动。
老疤备了丰盛的早饭,手把肉、奶皮子、炒米、嚼扣、黄油和奶茶。我教永利用嚼扣和了一大碗炒米,加上黄油,一人造(吃)了一碗,又喝透了奶茶,浑身汗汵汵的。
老疤又端来了银盅子,倒上滚烫的酒递了过来:
“那啥,这是上马酒,佛爷保佑一路平安的……”
我俩接过盅子一饮而尽。
“哈哈!老疤呀老疤:‘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小子不会是给我俩‘送盘缠’ (给亡人烧纸送钱)吧?”
“大哥大哥,这话说哪去啦?那啥,壮壮行、壮壮行嘛。”
老疤抓住我手,满脸诚恳:
“那啥,大哥,雪太大,不是闹着玩的。千万千万别坏车,瞅着不中赶紧窝(返)回来啊,……拿上这两块奶豆腐,道上吃……”
我就势攥住他手,把钱塞给他,他推让,我正色:“酒菜和住店钱,煤是塞一盒烟在矿上装的,没花钱。我只许旁人搭我交情,我不欠别人情,别二阴地种山药——没有面啊(光照不足的土地上种的土豆吃着不面)!”

道虽宽,却盖了厚厚的雪,只凭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和感觉着雪下边的搓板路慢慢行驶。
疤痢眼儿的话竟成谶语,我们的车在茫茫风雪中刚走了两个多小时便抛了锚。永利啷噹着着脸㨄起机器盖子,摘下风帽子(空气滤清器),说是气化器里边有毛病,找工具修起来。
我明白,在严寒中如果半个小时修不好车,也就是发动不着车,就得放出循环降温的水,如果不放水就会结冰,冰会膨胀而使发动机缸体开裂而报废。涉事司机就会被处以“开除留用”的惩罚,每月只开最低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与“搞破鞋”一样严重的罪名,终生抬不起头来。而放了水就意味着车不能行驶,人也被困在风雪中,更直白点说就是冻饿而死。
天冷风硬,又下起雪来。永利担心在半个小时内修不好车,更加紧张,在参差的部件中碰破了手,流着血赶修……
我瞥一眼裂了蒙子的破手表,沉痛地开口:
“永利,半个点儿了,放水吧!”
永利狠狠地在左车膀子(叶子板)上搥了一拳,无奈地拧开了放水阀,涓细水流象我俩生命的希望一样汨汨流失,感觉瞬间便流完了,我敢说这是我一生最揪心的水的流淌。
回到车楼儿(驾驶室)里,永利嗒然无语,继而哭了。
“完了,……咱们完了……都怨我,修不好车……我老妈寡妇失业的把我拉扯大,我死了她咋活呀……还盼我说媳妇呢……”越哭越伤心,竟呜呜涛涛的放了悲声。
我不哭,好象已不会哭。经历过66年亲属的自*、父母挨斗、多次抄家、同学的殴打和欺凌……死都不哭,绝不哭,更不能死,让歧视我的人捡笑!
下车攥了个雪球,咬一口……灵光一闪,我一下把半个雪球打到永利脸上:
“瞅你那熊样,还是个爷们儿不?我告诉你,咱俩死不了,知道吗?死不了!”
永利停了抽泣,张大嘴瞪着我。
“老兄弟,咱车上拉的啥?焦子(焦炭)啊!这玩意儿能烧、能烤火,能做饭,能把雪烧成开水啊!你忘了?我给同学捎了半袋子炒面,咱有吃有喝有火烤还能冻死饿死吗?还有脸哭呢?给我闭嘴。……赶紧干活,天黑就瞅不着了……”
有了生的希望,永利破涕为笑。我俩拿锤子、钳子、撬棍连砸带敲带掰,把马口铁作的加水桶改成了勉强能叫炉子的玩意儿;用喷灯点着了焦子;把所谓的炉子放到楼儿里大座子前边,把楼儿两侧下部的通风孔蹬开防止熏(xùn)着(供氧不足)。我们用类似日本兵用的猪腰子形的铝饭盒子舀雪烧开了,拌炒面吃的时候又有了惊人的欣喜,原来不是淡而无味的莜面炒面,竟然是用牛肉干反复碾压过锣的牛肉干儿炒面,还带盐精儿(有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