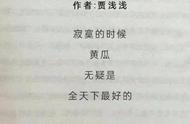—— 长 安 诗 社 | 解 诗——


百代红尘同一烹 | 长安解诗
劝君勿求长生药,勿为永乐耽行乐。
【长安小语】
2014年9月,武汉大学春英诗社的学术交流群里出现了一位名为“杜宛”的学妹,她的诗作“有长吉遗风”,引起了学长们的注意。其中有一首《神游曲》,当时在群里还讨论过。2015年10月,杜宛同学经过一年的揣摩与修改,又贴出了这首修改后的《神游曲》,诗社里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郭盈粟同学写了一篇诗评。本次的“长安解诗”栏目就以这首诗为解析对象。我除了加上一些简单的注释之外,“评论”部分都是由不愿署名的郭盈粟同学撰写的。
本期所解之诗,跟以往多有很多不同。以往多选七律,因为七律法度严整,容易从技巧的角度来分析。同样,本期的批评方式也跟以往相异,不是采用传统的解诗路数,而是偏西方的。对于诗歌的创作者和批评者来说,经常会面临两个很焦虑的问题。对于作者来说,生在前代许多伟大诗人之后,自己的语言和风格也极易受前人影响,导致迷失了自己的语言,不知自己的独特之处何在。这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影响的焦虑”。而对于批评者来说,也经常不能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符合作者的意图。如果作者是死人,那么死无对证,倒还容易。如果作者还健在,跳出来说:“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诗!”这就比较尴尬了。在这篇批评中,郭盈粟用了布鲁姆所鼓吹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批评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如今,除了古代文学专业的人士,对于一般旧体诗词爱好者来说,怎样评论、欣赏一首作品呢?除了找茬挑刺、训诂考证、钩沉索隐、分析技巧、互相吹捧之外,如何才能避免高中语文试卷“诗词鉴赏”式的那种“鉴赏”方法呢?又如何进行有深度而且精确的鉴赏呢?传统批评论的风格分析,往往是很简略的、提示性的。比如杜宛的这首《神游曲》风格学李贺,说一句“可以,这很长吉”就够了。如果是学周邦彦的,说一句“可以,这很清真”也够了。郭盈粟这篇评论,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含混的批评方法。
另外,后来我们才知道,“杜宛”就是春英诗社的梁文艳,江湖人称“豆腐”。后台回复“梁文艳”可获取梁淑美照及作品集,回复“郭盈粟”可看到郭盈粟的作品集。
游神曲
梁文艳
地若熔炉穹盖擎,百代红尘同一烹。神驰意造春千里,空空乾坤转大明。辇①动八方出白水,蛰兽昭苏冰雪死。裙铺三岛耀彤霞,丝履碾烂蟠桃花。老农呼儿起早耕,羸牛牵车呕哑行。宫人销夜费蜡火,恶龙盘盘啮金锁。贵贱相逢此尘笼,尘笼何处不春风。劝君勿求长生药,勿为永乐耽行乐。神仙无哀亦无悯,人间祸福皆一握。竦魂形兮立窅冥,句芒②吐气分清浊。清者迤逦上凌空,云气泱漭日曈昽③。浊者下沉潜阴壑,草树绵幂隐山泽。中有瘴鬼名魑魅,嗜食人肉折宝器。重幽叠邃猛虎藏,目夹金镜射寒光。赤岩峥峥青溪侧,云松烟萝千古色。徐甲无身白骨寒④,犹有痴儿夜烧丹。
【字词释义】
①辇:车。
②句芒:“句”读为“勾”。句芒是古代阴阳五行理论中的东方天神,其色青,于五行属木,掌管春天。
③曈昽:旭日初升、逐渐明亮的样子。
④徐甲:传说老子使徐甲变为白骨,又使白骨变为徐甲。
【评论】
私底下和F说,D的那首诗不是要人评价,而是要人分析的水平了。什么是分析一首诗?初学者常以为分析即毁灭,而被学院修辞折磨得忘了初心的老手,对分析也不会有太好的评价。而分析事实上是尊重作品,然后进入作品的一种方式。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值得尊重?能让人分析的作品隐含着它已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这常常适用于已经位列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是经过了剖析而发现了经典之为经典的理由呢,还是在被告知它是经典的情况下,想尽办法把老生常谈重说一遍呢?
I. A. Richards用过一种非常好玩的授课模式,他要求学生分析布置下去的诗作的特点,所有的诗作均隐去作者名字,里面既有大师名作,也有不入流的小作品,甚至还掺进了自己的诗。这种方法同时是对作品和批评者的考验。而印象式批评相比之下,就显得畏缩,走不出自己给自己画的牢房。好比男孩有一天学会了欣赏自己直观感受到的“漂亮”之外的美,而女孩面对世界,产生了拉斯蒂涅站在山丘上望巴黎时的那种心情。这都可以算是人开始成为人的一种表征,即通过学习把自身之外的东西纳入自身。
游神曲
A 1地若熔炉穹盖擎,2百代红尘同一烹。3神驰意造春千里,4空空乾坤转大明。5辇动八方出白水,6蛰兽昭苏冰雪死。7裙铺三岛耀彤霞,8丝履碾烂蟠桃花。
B 1老农呼儿起早耕,2羸牛牵车呕哑行。3宫人销夜费蜡火,4恶龙盘盘啮金锁。5贵贱相逢此尘笼,6尘笼何处不春风。7劝君勿求长生药,8勿为永乐耽行乐。9神仙无哀亦无悯,10人间祸福皆一握。
C 1竦魂形兮立窅冥,2句芒吐气分清浊。3清者迤逦上凌空,4云气泱漭日曈昽。5浊者下沉潜阴壑,6草树绵幂隐山泽。7中有瘴鬼名魑魅,8嗜食人肉折宝器。9重幽叠邃猛虎藏,10目夹金镜射寒光。11赤岩峥峥青溪侧,12云松烟萝千古色。
D 1徐甲无身白骨寒,2犹有痴儿夜烧丹。
这首诗用了长吉体,从用字韵式和整体氛围可以一下子看出来。如果用印象式的批评,或者说用点评这个词更合适,“有长吉遗风”,可能就够了。但这种点评,显然没有触及到作品的意义。硬要说有,那就是认为它不过是隔着一千多年袭用了一种风格,无疑是一种贬低。一篇作品理应像一个人,个体不是某个类的表征。况且它也根本没有说明白“长吉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风格,更不用说没有分辨眼前的作品和李贺的作品的不同之处了。这就是印象式批评的根本缺陷,它对自己所用的词汇没有清楚的把握,参照物和指向着的作品都是一团模糊。
歌行体往往用叙述做自己的骨架。可以把这个骨架看成诗人自觉地用某种客观存在来约束自己。诗人会表达一种观点,让它成为诗歌的主脑。正如现实生活中少有人对骷髅感兴趣,也少有人为别人的思想所吸引,肉体和衣饰才是注目之点,诗也是这样。我们看出来这首诗讲的是春回大地,它的主旨是对长生妄念的讽刺,而这两点并无吸引人的地方。要是对“春天来了”感兴趣,读读朱自清的中学课文就够了;从传统的主旨库存中翻出来的,没有了任何现实指向的东西,又有什么足以触及人心之处?当然,能按照格式来写诗本身是值得赞美的,就像我们称赞幼儿园小朋友把0-9这几个数字写得很标准一样。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用传统的主题和格式——来写。
这首诗的难点在于它典雅而精致,让人难以分辨它的时代。说它写得好,似乎只是说它写得非常传统。如果有人因此对它做出了较低的估价,就难以反驳。除非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今天写古典诗歌,写得好的标准就是写得像。我本人就不认同这个观点。所以接下来的分析集中于它的似而不似之处。
在这里春天的回归,在古典视野之内,是由神灵来驱动的。不过,与常规相悖之处是,春天不与创生相联系,而与毁灭相联系。A1-2还没有正式进入叙述,就笼盖性地奠定毁灭这个基调。接下来的A6和A8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似长吉而非长吉之处。李贺固然爱用“死”字,不过,正如钱钟书的洞见,李贺首先喜欢的是营造坚硬的意象,他诗句的构成好似雪和沙,而“死”正好能够把本来流动柔软的意象转化成坚硬之物罢了。而A6用死字恰好相反。它表达只是某物不再作为某物存在这样一个意思,在字面上与李贺相似却不是一个意涵。赋予春天这样一种毁灭性的氛围,无非是说,任何一次人间的转化,都源于神灵的残忍。这个神灵和传统上的神灵不大一样。A3-4第一次刻画这种神灵的形象,就显得无比空廓,如果把这种中国式的空间感不恰当地转换一下,也可以说它巨大无匹。A7就与这种巨大感相呼应,或者说坐实了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巨大而非空廓,而A7-8刻画的神显然高于或者说大于传统上住在蓬莱岛的神仙。这种残忍,或者干脆说这不在意的神就是乾坤本身,而它的不在意把神仙也笼括在内了。
B1-2和3-4都是为了5-6这一句话。在这一首诗里,它要靠这个脉络来获得意义,但一首诗的每一句,都有挣脱它所在的整体来获得更多含义的可能。李贺涉及神灵的诗没有这么有泥土味儿的句子。我们突然从一个高迥难及的神灵视角跌了下来。之前的春天虽然一反常规是毁灭的,但不妨它美而不可捉摸;现在的春天却如此现实,预示着一个新的痛苦的轮回。而基于我贫乏的经验,这句诗和A部分的配合,是夜莺颂第三节从现实逃逸到幻想世界的倒置。而从幻想到现实的跌落,也就暗示着这个幻想世界并不值得留恋。的确,一个专司毁灭的世界没有值得留恋之处。我们还可以再设想一种可能性。
一般而言,作者对他自己的虚构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信。极端而因此清晰的例子,巴尔扎克会和同伴聊他笔下人物现如今的际遇,而福楼拜尝到了毒药的苦味。现在我们设想一位作者设计了一个不合逻辑的世界,比如,在他的想象中事件A的发生导致事件B绝不可能发生,但他偏要写下事件B。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彻底的虚构,作者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笔下的世界。
现在再来考虑读者。所谓文学,就是“读者会暂时悬置对它进行真假判断”。而对某种文学,读者时时刻刻都在判断“这里说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的。比如我们读一本穿越小说,当然确定“穿越”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但对穿越之后的各种日常,我们会认为“在穿越这个前提下,这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种绝对虚构的罕见例子。对于A3-8构建的世界,作者(很可能)是不相信的,而读者也不会认为它可能。即便接受神灵驱动春天这个前提,接下来种种毁灭性的意象,也有悖于我们的认知。在今天写古典诗歌,尤其是因写得像而写得好的诗,不得不面对这悖论。无人相信之物自然是不可留恋之物。
B1-2写的是轮回着的痛苦,3-4则是持续着的绝望。4加重了“玉匙不动便门锁”的语气,而与其说它脱胎于“金蟾啮锁烧香入”,不如说和童话故事里看守着公主会喷火的恶龙一脉相承。而当我们看到拉平了人世贵贱的不是这种痛苦绝望,而是残忍四月吹来的风,不免有点惊讶。春风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操劳,带来的是由环境和心境的反差而加倍的绝望,它的字面和它实际所指的东西成了反讽。而就在这之后,我们见到了主旨句。
把主旨句放在这里,借用本居宣长夸源氏物语的话也不过分吧:把最想表达的东西既不放在开头,也不放在结尾而在中间,真是高明的写法。尤其考虑到一句一转的用韵,这个句子不管出现在哪都不受脚韵的催迫,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布局。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及时行乐?
要么有一种可感物比如酒,可以为及时行乐作担保。这里字面上的春风倒是可以做担保,但它的实际意涵拒绝做出这种担保。要么是认识到永恒必然的虚妄,仅凭这个转向到它的反面,满足于暂时的偶然的东西。看起来合适的回答是后一种。不过,从B3-6里我们只看到了轮回着的痛苦和持续着的绝望,完全没有哪怕一闪而过的快乐的例示。
现在韵脚难得的连贯了,暗示着一种连贯性的认知。可我们看到,这里的神灵不带任何感情地指向这个世界,而他成就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看起来也完全在乎骰子一掷。他不可取悦不可威吓,善人的祈求无益于善,而恶人的肆无忌惮也无损于恶。如果一个世界相关于神灵,那这个世界的价值也相关于神。譬如荷马史诗虽被哲人诟病为渎神,但我们也知道,在那个世界里,神是有所喜悦的。而在这里,神即是无常。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为及时行乐提供担保的是某种形而上学。
我们认为长生不可能,认可“莫求长生药”,不是从诗歌构建的世界出发的。现在强迫自己从诗歌的逻辑认可这句话,那就是,人不可能获得凌驾神的力量,而神是随时都要进行毁灭的,因此长生是妄念。而我们认可及时行乐,也未必是从诗歌的逻辑出发的,现在要做一样的事。及时行乐并非因为快乐本身,而出于对神的诅咒。快乐被毁灭之后是痛苦,而痛苦被毁灭之后可能是加倍的痛苦。这样就显出了快乐的特殊之处,快乐是和神的抗争,也是一种自我折磨。因为在人的世界,赋予了价值的快乐哪怕只有一刹那,人也可以认为它是永恒;而价值的来源只能是神,神拒绝赋予人类世界以价值,那么,一刹那的快乐只能是一刹那。而且快乐随时会被夺走,快乐不能不伴随担忧;失去快乐之后品尝到的是痛苦而痛苦,快乐就只能是自我惩罚。我们管这种自虐狂式的快乐叫放纵。
在段落C值得注意的是,“浊者”是“清者”的四倍长。当天上由黑暗渐渐转向光明,地上,人所生活的世界更加陷入绝望。魑魅嗜人肉,则猛虎同然。而人的彻底毁灭,也被漠然静观着。
D是全诗最显得跳脱,无理的句子。C-D这两环是怎么扣在一起的?看起来就是骸骨这个意象。是则举世而大梦,而梦醒时如同噩梦。这种深切的恐怖感在古典诗歌里应该很罕见吧。现在应该想想办法把这个梦颠倒过来了。徐甲这个故事,要是交给芥川龙之介来重写,没准会把老子写成要赖账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汉吧。而徐甲自己又焉知自己不是本为生而化为死,就那么简简单单地承受?幻觉就是这么一种上手的东西。既然生之为死是幻觉,那么死之为生同样可以是幻觉。既然身在幻觉之中无法分辨,那就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幻觉。老子固然可以把我一切都剥夺,在我失去意识前那一刹那,也要认为他不是把本来属于我的还给我,而是夺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如果说有错,那个任意玩弄生死的人早就犯错了。
对于神的设想也一样。既然设想了一个随时会施予毁灭的神,为什么不设想一个随时会赋予价值的神?每一次风撩起帘子,都是神会走进来施予拯救的时刻。我们只是稍稍修改一下人设。
这首诗有很多属于现在的东西,可在进入现在的时候,还是裹挟着传统的东西。比如那种可怕的权威感。如果我们不再承认神仙传里的老子有什么权威,徐甲就该获得他的工钱。和权威伴生的惩罚,无缘由的毁灭,也就没有承受的理由。试想如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斩*恶龙的英雄,但如果公主不自己走出来,那情况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
分析作品最好别涉及作者意图。分析就在身边的作者就更是如此了。他只要一句话,我不是这么想的。说多少就都成白说。为了挽回,就只好说,我针对的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意图。就这样我自鸣得意地把作者拉进了精神分析的领域,可以肆无忌惮地胡说。精神分析能有意义,只能是接受治疗的人按医生的话来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而诗人,如布罗茨基所说,下意识对他来说不存在,因为他已经把它穷尽了。诗人当然有理由拒绝精神分析,批评者也最好有这个自觉。
撰稿 | 郭盈粟 长安小语 | 范云飞 编辑 | 凌篁

长安诗社 | changanshishe
缔 · 结 · 高 · 校 · 诗 · 词 · 阵 · 营
投稿:changanshishe@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