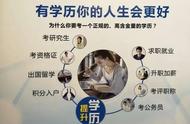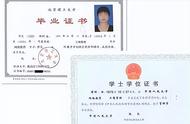德国的教育分轨制稳定供应高素质技术工人
很长时期,德国的学生就是在10岁时确定了受教育的学校,乃至终生的职业方向。但在现当代,这种制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认为如此大事通过一次考试来决定,似乎包含了过多的偶然性,更认为10岁决定终生太早了一点。于是1959年动议,1964年《汉堡协议》确定,5、6年级为观察和定向的阶段,就是说,将分流的门槛推迟两年,将分流的决定做得细致些。1973年联邦政府甚至表示要建立独立于学校类型的定向阶段。这一方案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它挤压了文科中学的完整的教育时间。
德国教育早期分流的根据是,多数人在10岁时已经表现出日后的潜力。早期分流的收获是可以缓解竞争,让潜力弱的人退出竞争,给潜力强的人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代价是,晚熟的人可能遭到淘汰。

任何制度都有自己的优劣,德国无疑是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之所以成功,依靠的就是大量的技术工人。这也是德国分流制教育的成功。中国的教育者也有提出要学习德国的三轨制教育,提升国民素质,但是最终都消寂于无声,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在此仅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聊起。
科举制已经废黜一千三百年,但它的影响仍影响至今。中国人没有什么明确的信仰,但是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情结”,传统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中看一下中国人的“学历”情结。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之程度上难说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又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不错,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上的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合法性的程度显然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更迭,科举制贯穿1300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护。顾颉刚说,它“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此话颇耐寻味。科举明明是帝王建立的,故其后半句隐含的意思似乎是,帝王会干涉他自己建立的制度,但他未干涉科举。前半句似无争议。寒门子弟借此跃然而上,拥护自不待言。而科举分明是皇权借以消除门阀垄断,贵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风。清代旗人不考科举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羡慕汉人的状元科第,便有人学着做(八股),曾经乾隆禁止过,但还有偷着做的,后来才开了禁。”唐僖宗乾符年(公元875年)有敕令:
“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
以后这个观念深入人心,逐步演化为清代人所说的“正途"。其实当时从官的路径还有几种:军功、荫生(祖、父有功于国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孙为官)、捐纳,等等。为什么独独科举是“正途”呢?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张仲礼说:“异途’出身者……他们主要是先捐监生,然后捐得官职的。”“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为何军功不是正途?齐如山说:因为“军功有假的。统帅所保之人,自然有许多实在是有功劳的,但也有统帅的亲戚朋友下人等等,虽然未到战场,也可以夹杂保上。因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被社会轻视了”。 荫生中无学识者甚多,故被鄙视。

科考现场
由上述可见,第一,正途在于国家重点看待;第二,或许是更重要的,民意以为那是正途,其支点是公正。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由此可以得出,虽然科举已经被废,但是如何通过正途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地位,这种思想仍然根植于人心。高考虽然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但是其底层逻辑是“公平、公开、公正”,所以凭借高考获得“功名”就会被中国老百姓看的极端重要。作为反面,只有高职高专学历或者随后通过自考、成教、电大、函授、远程教育等方式获得大学学历,在老百姓眼中、在企业老总眼中就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因为感觉要么你能力差,要么是通过不公平手段“上位”,终究非“第一出身”。
中国传统分流制的终结注定我们的孩子必须走高考这座独木桥教育的早期分流不可能被德国人垄断。德国人早期分流的特征在于其严格的制度化。与之对应的是“自然的分流”。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等级观念是德国人在二百年前能确立教育分流制的缘由。要在同期的美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里没有阶级观念。但德国人的伟大,首先在于认清了分流必行后便任凭世风流转而固守这一原则;其次在于其令教育分流渐次走出了封建等级的阴影,转化为现代公民兴趣与才能的函数。而系列配套措施的建立,如两种类型的中等教育之间的通道,又如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的便利与技工阶层报酬的优厚,使其教育分流制精致、周全又历久不衰。
我们有着与德国人完全不同的历史与制度选择。自秦王政结束封建制,特别是自隋唐开创科举以后,中国社会拥有西方无法比拟的垂直流动的阶梯。我们至今没有德国那样的教育分流制度。但是在中国人漫长的科场博弈中,“分流”早就成为了家族的策略选择,且这一选择有极大的广泛性。因为考中举人和进士的超小概率,即令殷实之家也不会让其全部子弟扑向科举。又因秀才可以带给全家较好的尊严和地位,贫寒之家也会节衣缩食选出一个子弟敲科举之门。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了与德国近现代的“制度分流”相对应的“家庭分流”。二者异曲同工的是降低竟争的成本。中国当代教育中的竞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先人在漫长岁月中贯彻的“家庭分流”。
科举制度建立后的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家族兴衰迅速。于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成为金科玉律。人才辈出的家族遂被推崇。
晚清曾国藩家族正是这样的楷模。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早年失于检点,三十余岁后立志回头。从此“终身未明而起”。带领耕夫们将家里小片农田开垦连接一体,种植水稻蔬菜,养猪养鱼。致富的同时建立了治家之道。《曾国藩家书》中脍炙人口的“早扫考宝书蔬渔猪”便是祖父治家的口头禅。发达后曾家的妇女都坚持纺纱、做衣、纳鞋。曾国藩父亲曾麟书(1790~1857)历经16次童试(考秀才之试,亦称乡考)失利,43岁(1822年)方考中秀才。自知天分有限,后不再应试,专心致力于培养其五子。日后子辈出外闯荡,他闭门栽培孙辈。
曾国藩(1811~1872),1833年(约22岁)考中秀才,翌年中举人,1838年(约27岁)第二次会试考中进士,入翰林。

曾国潢(1820-1886),1845年与弟赴京,在兄督导下学习。1846年(约26岁)捐纳国子监监生。此后无意举业,回乡专心辅助父亲照料家务。曾短期助兄训练乡勇,父病归乡。父去世后全面主持家务。
曾国华(1822~1858),曾童试失利,1846年(约23岁)捐纳国子监监生,后几次参加乡试(考举人),均告失利。36岁时死于与太平军之战事。
曾国荃(18241890),1847年(约23岁)考中秀才。秀才分三等:廪生、增生、附生。曾国荃1848年获科试一等,补为廪生。1854年选为优贡生。旋即发生的战事中断了曾国荃的科举之路。其日后的地位来自军功。
曾国葆(1828-1862),1848年(约20岁)通过了童试的前两关县试和府试,但院试未过,厌倦科举。1851年勉强参加,再告失利。父兄均支持其选择,从此告别科举。后加入湘军,34岁病故军中。(以上参阅成晓军,2006)
曾国藩有两子。
长子曾纪泽(1839-1890),在1850年咸丰登基时被恩封二品荫生,即不必经童试即可直接参加乡试。1859年(约20岁)乡试失利。曾纪泽非不通国学,且研习过天文、算学,粗通英文。在曾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时,曾国藩慨然同意。
次子曾纪鸿(1848-1981),于1862年(15岁)在湘乡童试的县试中获榜首,且从其日后参加乡试看,他应该是考取了生员的功名。以后1864年(16岁)、1867年、1870年三次乡试不中。1870年朝廷赐其“举人”。1872年祖父去世,同年几个月后他完成了《对数详解》(五卷)。1874年他推算出圆周率一百多位,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日后李约瑟给予高度评价。
从曾国藩家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清代以前,中国大家族制有明确的“教育分流制”,但随着“一孩儿制”的要求,这种分流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