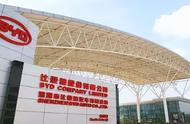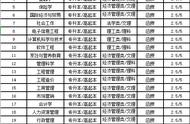昨天回去给父亲过生日,我们晚上六点才聚到饭店,九点多的时候,我母亲就催我和老公提前走。我们要回市里,离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是提前给父母打过招呼的,因为第二天老公还要加班,只有连夜再赶回去。
01我们是从饭店直接走。已是初冬时节,晚上又飘了雨星子,有急急的风,一推开门,就打了个寒战。我赶紧裹紧身上的大衣,示意大家不用送,再热闹一会儿。母亲从正掩上的门里紧跟了出来,叫我别急,说给我带的有酸菜,就叫了二妹一起出来,跟着一起到停车场,打开二妹家车后备箱,给我拿回来三个手提袋来,风一吹,袋子里一股熟悉的酸菜味儿扑过来,知道是老妈给我带了酸红薯叶儿;妈说另外两个袋子里,一个是菠菜,一个是白菜,她知道我好喜欢吃菜馍,本来都带着做菜馍用的菜,打算下午的时候在三妹儿那儿给我烙几盒,走了让我带走,可三妹子让她别惯我这毛病,让我自己把菜拿回去,学着烙。

“你三妹说,她和她二姐都会烙,只有你笨,就是做得少,多烙几回,也就学会了,我总不能给你烙一辈子,你还得自己学会了,啥时候吃,都不难。”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笑,爽朗的声音在有风的夜里传得很远。
02到家已经十点多,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些事儿拿回来放在冰箱里。房间里已经供暖了,放在屋里到明天菠菜就蔫儿了。把菠菜从袋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菠菜已经洗净,而且只有叶子,根儿也已经去过了,应该是专门晾过了,没有水,新鲜水灵的样子;另一个袋子是一颗包心的大娃娃菜,一看就是买的,今年我父亲的身体不是太好,妈就没种几样儿菜,菠菜里还混着一小撮的香菜,细细的,我想起来,应该是在楼顶大花盆里种的那点香菜,妈应该是全部拔了,给我洗净,拿了来。
菠菜和香菜都不稀罕,市场上有的是,只有这“酸红薯叶儿”才是我最惦记的。
菜馍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也是常见,里面放的菜也足够丰富,有茴香韭菜、韭菜鸡蛋等等好多样儿,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正宗,夏天的苋菜菜馍和红薯叶儿菜馍很是稀罕,反正我是在附近的摊贩那里没有见过。苋菜是学名儿,在我们那儿,都叫她玉米菜,也不知道为啥它跟“玉米”有关系,但也许与这俩字也没有关系,因为在家乡话里,玉米也是大名儿,小名叫“秫秫”,所以说具体是哪俩字还值得推敲。
但重点不在字,在味儿上。家乡的苋菜有圆叶的,圆叶的又分红苋菜和绿叶儿苋菜,尖叶儿的也有,用来塌菜馍的,我妈最常用的就是沟里坡沿到处疯长的野玉米菜,也就是野苋菜,要说这种菜也是奇了,不用撒种,年年长,夏天做捞面条,没菜了,要么在路边随手揪几根红薯叶儿,要么就是掐几把野苋菜。

要想做菜馍,那得去河边,河边成片长得都是。夏天我回去,妈总会提前去河边掐来最嫩的野苋菜,洗净,像给我带的菠菜那样,先晒着,等塌菜馍的时候,就不是湿塌塌的。红薯叶儿常见,四野里都种得有,谁家的都可以去摘,家家户户都有,不稀罕。
这两样菜塌起来不用放任何调料,就是用井水洗干净的菜,控干火分,直接切了,不用太碎就行。;和半烫面,当然也可以温水和、冷水和得更筋道些,适合牙口好的年轻人,我现在喜欢用半烫面烙的菜馍,吃起来柔和软香,劲儿的很。
面和好了,不急着烙,放在面盆里盖上湿抹布饧一会儿。
快到饭点儿了,灶上煮的稀饭也好了,稀饭是烙馍的标配。有时候是绿豆稀饭,有时候是小米稀饭、秫秫糁稀饭。
稀饭起锅,放上铁鏊子,现在都用平底锅、电饼铛了,可我妈还是习惯用几十年前安徽铁匠师傅来村里打的鏊子,鏊子经年累月的月,不知道烙了几千几万张馍,已经被煤火熏得里面包了黑灰浆了。
有时候一不留神儿,被妈用小擀杖擀得圆月似的烙馍上着上一点黑,妈却说这烟灰不脏,习惯了,觉得那的确不脏,而且似乎偶尔看到那团黑,就想起小时候用锅灰抹的大花脸儿来,那圆月似的烙馍也变得调皮可爱起来。

先烙好一张锅,放在用高粱秆子结成的圆秕子上,上面提前均匀地撒了玉米面,省得粘上。在第一张烙馍上摊上厚厚的菜,然后再麻利地旋风一般地擀好第二张,就那种神奇,这一张放在菜上面,从上往下看,两张烙馍是一样儿的圆,一样的大小,妈用迅速地在四周按上一圈,一个菜馍坯子就好了,放在鏊子上,一面洛得起金黄的馍泡泡儿,用手托着,翻另一面。
两面都烙熟了,里面的菜还不是十分熟,这不打紧,也就三五分钟,第二个也做好了,“塌”在第一个上面,别急着,“塌”菜馍离不开“塌”,一个接一个地塌着,塌个五六个,最下面的两个就可以先拿出去吃了。
04前面提到苋菜和红薯叶做的菜馍,都是原味儿的,啥都没有加,吃的就是叶子菜特有的味儿。
灵魂在于调的蒜汁。家里自己种的紫皮蒜剥个几瓣,要小心,别抠到指甲缝里,得辣上你半天。把蒜和几片姜加了盐、青辣椒放在青石的蒜臼里捣成泥儿,用勺子舀出来,盛在小碗里,加入小磨香油、醋,再加一点凉开水,撒点味精也行,不撒也中,随便用筷子搅搅,把菜馍从下面抽出两个,摞在一起,放到案板上,用刀从中间一切两半,也可以是四块,用盘子放了拿到外面桌上,从那切口的尖儿上使劲儿揪出一大块,往蒜汁里一沾,吃一口,那滋味,一辈子,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