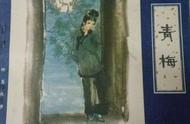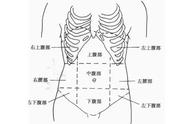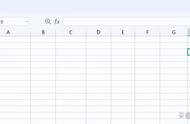作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老搭档,包括摄影师斯瓦沃米尔·伊齐亚克和作曲家普赖斯纳都参与了这部电影。前者为影片带来犹如浸淫在一片金色之中的画面效果,后者用华丽的音乐成功地将两位女主人公串在了一起。对影片的宿命般的宗教救赎涵义把握得极为精湛。
空灵圣洁的女声和幽远清越的笛声贯穿了整部戏,似乎荡涤着听者的灵魂,有着洗尽铅华般的神奇魅力。

《两生花》的外文原称是「薇洛妮卡的双重生活」,但中国观众更似乎喜欢用「两生花」。
从各个层面上来说,《两生花》都是一部自我反思的伟大影片。玻璃的反射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对这个关于在当代波兰与法国过着平行生活的两个年轻女孩的故事来说,显得十分适合。
它与基耶斯洛夫斯基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样,这也是部对“窥”和“讲故事”这两个行为进行思考的影片。这部法国波兰合拍片邀请观众反思那些令我们每个人与周围各种力量捆绑在一起的线索。
制片人莱昂纳多一针见血地将本片描述为“一部形而上的惊悚片”。
而本片剧本也正出自他与克日什托夫的共同手笔。

影片开场第一段戏为解密《两生花》提供了一把视觉上的锁匙。
1968年的波兰,黑暗的街道上下颠倒地出现在画面中,这是两岁的波兰薇洛妮卡的视角:
她母亲的波兰语旁白声响起,让她在将近圣诞前夜的冬季夜空寻找星星。下个镜头中,小女孩手臂向上指着,母亲双手抱着她,以便让她看见更多东西。
镜头切到1968年的法国,画面被一个小孩的眼睛占据:她面前的放大镜被移开,我们发现“看”这一行为本身再度成为画面中的关键。她母亲的法语旁白声响起,让女儿审视一片树叶,我们还听见小鸟的鸣叫。
很明显都是在春天,说明影片头两段戏并非同时发生:波兰薇洛妮卡的故事先于法国薇洛妮卡的故事——或许波兰薇洛妮卡的故事也是在为后者的故事作铺垫。

火车缓慢地前行,阳光透过玻璃窗温和地弥漫进来,金黄色的幽雅的色调。
她靠在窗边,孤独而又柔美的微笑,修长的手指划过的是弧度的感伤。
轻轻转动的光滑圆润的玻璃球,在阳光的折射下好似也有了温度。一片片窗外的景物同样缓缓地掠过,树木、天空。有种眩晕的错觉。让一切规则的事物变幻,变幻。
挤压在拢仄的空间里,既而突然感觉到内心深处隐隐的感应,时空却已经一换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