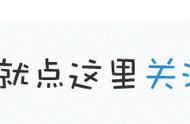我家房子后面有片地,婆叫它后坟里。
后坟里是块缓坡地,从东到西有十多亩,原是一片坟茔,埋葬了许多村上人的骨骸,也包括我们杨家的祖先们。
婆这一代人,把许多地方都称作“里”,如村东有一所小学校,原是原杨家祠堂的所在地,就叫“祠堂里”,村西北有块平地,叫“后平里”。里,从土,从田,在这里含有区分界域的意思,实在是古雅的用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用到称呼某个地名了。
我们杨氏族人,来自于何处,不得而知,据先祖们讲,是山西洪洞县移民,但是据我猜测,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老庄子在北宽坪庙湾村,从北宽坪到夜村聂沟,再到沙河子任家后村等。北宽坪本就是三县交界地方,东临丹凤,北接洛南,可以上关中,也可以下河南、湖北,华阴杨南迁,抑或湖北移民也未可知。
我杨氏祖先来到商州任家后这块僻地,当时可能并未开垦的土地,依山而居,开垦前面不算平整的土地,开枝散叶,房屋便由北向南扩展开来,形成了这么个村子,有了东边的戏楼和杨家祠堂,村前韩湘子庙,王山上寺庙和龙泉寺的庄观,有了看病的秦先生,教书的李先生、舒先生等。“葬我于高山兮”,也就有了埋葬先人们的“后坟里”,有了杨氏族人区别其它先民“边界线”,从前熙熙攘攘,现在没落,依然存在的杨巷。
杨巷在后坟里的西边,是村上连接南北的通道,长约三里,宽约丈余,弯弯曲曲全部用青石铺就,两边是石砌边沿,村上再找不出象其它一样浩大工程,而且经历上百年依然保留完整的巷道了,可以想象先民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在巷道的东侧住着我们杨氏族人,西侧则住着李、任、于等杂姓人家,也可以想见当初的开垦者们经历怎样的矛盾冲突。现在经历上百年融合和通婚,族姓而居早就没有了,但是,只要看到杨巷,老房子归属还是可以大概分得清的。
在长坪公路和会峪到北宽坪路没有修以前,杨巷是上关中,下河南、湖北等最近便的“大道”。上上个世纪许许多多的大事都从杨巷子和后坟里经过。有成群的的兵匪,经商的贾人,退休的官员、赶考的举子等各色人熙熙攘攘穿过杨巷,走过后坟里。在父辈的口中,我得到许多关于他们对于杨巷和后坟里的记忆。
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祖父作着这个村的里甲长,也就是现在的村长。在“兵来如梳,贼来如蓖,官来如剃”的年月里,无论官兵还是土匪,受到了打击,钻进大山,都可以向邻省邻县撤退或逃窜,也只有到了这块地方,才能得到喘息的机会。祖父们就在这后坟里组织“劳军”。一桶桶热腾腾的糊汤面,倒在笸箩里,笸箩就一字排列着就放在后坟里靠近杨巷较为平坦的地方,旁边放了碗筷和辣子、盐、葱花等调料,队伍过来时,这些人就用碗舀了边走边吃,吃完了在另一笸箩再舀,吃毕了碗就放在地堰上。
村上的许多年轻人,也正是从后坟里出走,舀着糊汤面吃了跟着队伍“背枪”。是跟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正规部队还是土匪,“当兵吃粮”谁还有机会考量呢?有不幸战斗中死亡的,有下落不明的,有后来享受政府津贴的老红军,有后来被遣返回家,在之后历次运动被批斗的“反动派”……我的叔曾祖杨天菊就被土匪寻仇,*死于杨巷,葬在后坟里。杨委生先作着土匪,后反正参加民兵,被土匪砸死在碾子凹,1982年被评为烈士,我的那个出了五服叔伯杨长闻随中原突围部队出走转战南北,后随王震将军的队伍入疆,一直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工作,做官到副军级……
父亲小的时候,在后坟里揭堰捉过黄老鼠子。都到了商县临解放前一二年,父亲光着屁股站在后坟里,村上有人吓唬他:“粮子来了割娃把子!”,父亲吓得哇哇大哭。
后坟里满目荆棘苍莽的摸样,在我脑子依稀还存留一些印象,但是也不外乎长满了带刺的灌木,草深,高低不平而已。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村上兴起一场“平坟”运动,挖平了后坟里,来不及收拾的骨骸裸露在外面。在村民休息的时候,我和小伙伴用草穿了头骨的鼻孔或眼睛,木棍抬着把先人的骨骸扔到干枯的尿池子里,忙得不亦乐乎。姐姐已经上了学,很神秘给我说,孙悟空未打死的白骨精就出没在后坟里,白骨聚集一起就是妖怪。那是村上没有电视机,我没有动画片看,仅有几本小人书,我却不识字,也轮不到我看,对于白骨精和妖怪敬畏与恐怖我是一点也没有。直到多少年之后看到电视“神剧”《西游记》,配上恐怖音乐和动画特效,白骨聚集幻化人形,我才感到有些可怕,感受到教化的力量。
挖平了的后坟里先是用作了耕地,种些玉米高粱,后变成民兵打靶的靶场,再后又在西边靠杨巷地方盖了房子,买了电动机器,用作了农作物加工的作坊,房子后面盖了猪舍,但是好像一直没有猪养。之后靶场变成大队的晾晒场……挖平了堰畔,先人们的坟墓原先到底在那儿也不确切,村民最初几年还是凭着记忆位置聚拢了几个坟头,逢年过节祭祀着,后来看到实在恢复不了,也就认了,每年依着记忆位置烧纸和挂纸把。
挖平之后的后坟里地方变得开阔,出后门就到了,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成了是我的乐园。家里人忙于地里和家里的活计,没有人管我们,后坟里三天两头的变换,吸引我一帮小孩看热闹。未上学以前,我整日在后坟里和杨巷之间奔跑着,和一群小孩打闹。累了,就倒在后坟里草垛中睡着了,肚子饿了,就后门回家,抱一碗不知什么时候的剩饭喝,或者啃个干馍烧饼就一瓢凉水,跑回来继续耍。难得有清静的时候,躺在草丛中,看天上云散云聚,听近处鸟鸣虫啾,庄稼拔节,蚂蚁打架,蝴蝶翻飞,蜜蜂采蜜,远处鸡鸣狗叫……一把泥土也可以把玩半天。直到夜幕降临,星星布满天或者月亮爬上树梢,婆一声声喊近了和急促了,也才恋恋不舍跟着回家。
我的两个叔伯小姑,比我要大一两岁,也没有上学,在后坟里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下,总喜欢扮演哭丧的角色,常常拉了我去凑数。她们其中一个平平地躺在地上,闭着眼睛,身上和脸上盖着一层青草“装死”,另一个则用毛巾或布捂着脸哭嚎,哭一声,头低一下,手拍一下地:“我那可怜的亲人……你啥都没交代就走啦……你叫我咋办呀……”我被她们安排扮作“孩子”的角色,于我而言是本色表演,但是要苦着脸,低着头,要抽抽搭搭地装哭,我却总是扮演不好,呆呆看着她们表演,理会不了。可怜我的那个哭丧的小姑,竟然由此成谶,命运从此埋下苦命根儿。多少年后相继嫁了两个丈夫,都意外得病而死,死得很突然,一个麦忙天喊头痛,叫了乡村医生扎液体,打着打着就死了。招了女婿,过了七八年,也是夏天,在去年大概脑溢血也死了。我奔丧回去,竟然惊异地看到,小姑跪在尸体旁,白布蒙着脸,哭天抢地,哭的“我那可怜的亲人……你啥都没交代就走啦……”。五十出头的人,容颜竟然象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我喜欢玩的游戏是打仗,领着一帮同龄的小孩,封他们作一官、二官、三官……在后坟里用玉米秸秆打打闹闹,想着在那儿挖成电影《地道战》那样的地道,把敌人消灭在地道里,用铁扫帚(一种植物,茎秆农村人扎作扫帚用)打造出“青纱帐”,给“敌人”突然袭击,遇到追击,我们能够迅速脱身。说干也就干,带上一帮小孩在后坟里一个堰畔挖了一个下午,遇到大人干涉,自己也觉得不像那么回事,也就作罢。我喜欢作着“角色”的导演,自己不出头,作着“狗头军师”。很羡慕电影里“大盖帽”或者背手枪、挎指挥刀者的威风。一次随父亲进城,偷偷拿了父亲三块钱,又偷偷去了那是工农兵商店,隔着橱窗,犹豫盘算了好久,放弃买“机关枪”想法,买了玩具望远镜和“黑墨眼镜”,大概是觉着这两样东西可以配得上我用迎春花杆或着杨柳条撑起的黄帽子作“大盖帽”,更符合我“指挥官”的形象吧。
我七岁多了,好说歹说我都不去。后来觉得不去是不行了,磨磨蹭蹭也要把我黄帽子用杨树条子作的“大盖帽”撑圆压平。我就是戴着这样的帽子由婆背着进了小学。认了几个字,我家的房门、围墙、厕所等就用粉笔写上了“xxx革命政府”、“第一营房”、“国营第二食堂”,“打倒任小红”等字眼标语,门楼上钉着用“红宝书”包书塑料皮剪成五角星,窗囱也挂上了用姐姐红领巾扎成小红旗。
在后坟里打闹的日子是快乐而短暂的,分田到户之后,后坟里的农作物加工场作价卖给村民任全文,猪场卖给任百社,他们都从新盖了房,其余的土地卖作村民的晾晒场和打麦场,后来陆续成了几家宅地盖了房子。“后坟里”这个地名再也没有人叫起了,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按人的住处论了,说着“到全文哪儿”,就是到了后坟里西边,说着“永文那儿”就是后坟里东边。
由于杨巷全部用青石铺就,挖掘不易,两边都是房屋,机械施展不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山庙拆了又重建了,但是却始终难以恢复旧的规制。村口的湘子庙也被逐渐蚕食着作了村上医疗站。庙门口生长了几百年,三四个人合抱不了大药籽树,树干已经中空,也被人一把柴草放到树洞烧死了,当年看病的秦先生手植上百年的银杏树也不知被卖移到那里了……杨巷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只是在周围高大房子的掩饰下,显得那么窄弊。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绕村从后坟里经过,算是把这几户人家连接起来。
杨巷已经没有多少人走,走在里面,半天碰不到一个人,周围残垣破壁,象是进了“鬼蜮”。后坟里几户人家常年在外打工,有的已经在其它地方盖房或者买房,房门常年“铁将军把门”,很多时候没有人居住。
多少年前清明,我还在后坟里某个堰坂给老先人烧纸,后来也不去了。
后坟里,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记得它原来的这个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