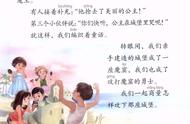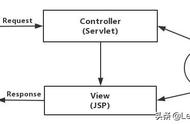杨仲义不仅是北路梆子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而且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路梆子传承人。作为北路梆子当代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剧团领导,他承担着传承北路梆子的重任。
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他是在2003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当时他带团正在五台县上西村演出,我们陪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位专家到现场实地调研剧种剧团情况,因他当晚有演出, 我们只作了简单的交谈。转眼7年过去了,再一次见到他是2010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把他约到省戏研所会议室里。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开始长谈,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因为他另有安排,我们相约择日再聊。
7月中旬,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未完成的采访。
笔者:您现在是著名的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也许是相同的,但他们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和从艺经历却各自不同,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是怎么走上戏曲之路的。
杨仲义:我1961年出生在山西省保德县黄河岸边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因为河曲、保德是山西、内蒙、陕西三省的交界地,河对面就是陕西府谷县,当地民间文艺很丰富,晋北、陕北的民歌、二人台,都在黄河流域交融流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我们那里民间文艺积淀深厚,我的父母或者说我的家庭受当地民间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我们这个家庭称为一个民间艺术之家,应该是不为过的。我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贩,很喜欢民间文艺。过去从保德县城关到河曲旧县八九十里路,他每天肩挑扁担往返于此。听我父亲说,他走一路唱一路,唱的小调山曲几乎可以不重复。 每年的正月ニ十五、六月六这些传统的古会,都要踩高跷闹秧歌。我父亲也是表演好手,既是组织者,也是表演者。我母亲也会唱,而且嗓子特别好,人很灵慧。我们这一辈兄弟姐妹七人,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我大哥杨仲青,1986年参加过全国的民间音乐舞蹈大赛,现在已经从保德县文化馆退休,他他唱民歌非常好,我二姐杨爱珍也是唱民歌的,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得过大奖,当时《山西日报》还有宣传他们的文章,我承父辈基因小时候喜欢唱歌,而且嗓子也不错,我受哥哥姐姐的影响比较大,儿时他们就经常教我唱歌。
我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也不好,上艺校可以解决家里一口人的吃饭问题。从方方面面考虑,1974年忻州艺校招生,经过几次考试就被录取了。
刚考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唱北路梆子,那会儿年龄小,还不知道北路梆子是啥,反正就是喜欢唱歌,以为到了学校学声乐,结果是唱戏。一开始也困惑,想学唱歌结果唱戏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后来想,学戏就学吧,起码能吃饱,不用花钱,还给发些东西。当时在家里天天吃红面还吃不饱,学校每天还能吃顿白面,一年还发两身练功衣,一个月还有一块多钱的洗漱费,觉得挺好,生活问题解决了。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戏生涯。学戏很苦,但我从小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所以不怕吃苦。别人练一遍,咱就练三遍五遍,别人因为疼不练了,咱能忍住疼继续练。就这样,我的基本功打得比较扎实。
那个年代我们从外界获得的信息很少,学戏精力非常集中,自己投入很多,干一行爱一行,争取在这一行做出成就来,思想比较简单。认为能上戏校是很光荣的,社会很高看,自己很自豪。全班15个学员,老师比我们还多,一个学生一个半老师,每天七节课,实实在在的学了五年。搞戏曲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进来,你都不可能做得很好,她是玩人的艺术,就是用自己身体的四肢五官来打造艺术作品,展示给人们去欣赏;她是脑力体力的结合,用大脑指挥身体去构造一件艺术品。出一个好戏曲演员很难,俗话说:“五年胳膊十年腿,二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太难了。
现在社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接受的信息多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天天重复死练这些东西。有时自己也有感受,我能不能坐下来,我在以前那个环境里能做到到专心,现在我还能不能做到,再说做到了又能得到多少认可,你的付出又能得到多少回报。有时候会有这种苦恼,但我又觉得,戏曲是最有中国气派,最有中国文化神韵的集大成的艺术。中国戏曲,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演体系,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无愧的、灿烂的、辉煌的。这又给我信心。我们国家应该很好地保护它,这是我们本土的好东西,她可以激励民族自豪感。如果消失了,中国文化就损失太大了。
笔者:对戏曲院团的改革国家很早就提出来了,并且制定了一些政策方案,您对改革问题怎么看?
杨仲义:改革就是要让能唱的人、唱得好的人、愿意唱的人好好唱,让不能唱、不愿意唱、不适合唱的人给他一个出路,给他一个分流,给他一个安排。现在混饭吃的多,假冒伪劣的多。剧团养的啥也干不成的人多,这是多少年形成的,改革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拖得谁也不能好好干,势必这个行业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有的人挣着公家的钱,公家的活不干,到外头搭班挣钱。与其这样,不如该养的养,该放的放,把不想*人全部放到人才市场上去,让他们彻底放开去干,应该把这些通过政策明确起来。我们的改革有些不明确,我们基层剧团无所适从,日子很难过,叫不起套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胆大的不是今天请假就是明天有事,团里的工作不好好干,成天到外头干,团里还得给发工资养着。那些老实的循规蹈矩的,生活过得苦苦巴巴的,三年五年坚持下来了,十年八年忍过来了,二十年能不能坚持下来,现在就到了要崩溃的时候了。
我作为一个领团人,作为一个多年来为戏曲付出的从业者,希望我们这个事业发展得好、发展得快,生存得无后顾之忧。对改革我是支持的。市场经济多少年了,改革开放多少年了,我们应该改革,但改革必须实实在在地、认认真真地、慎重地改,必须务实,而不只是形式和口号。比如一个企业,它得要产品,它得要效益,它得养活人,这是实的东西,产品有没有,效益有没有,人们活得怎么样。这些问题怎么考虑,落到实处没有,围绕这些问题怎么具体操作,我们很心焦、忧虑,但是没办法,很多关系理不顺,剧团在改革中主动性很小。
我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30多年的文艺工作者,从自己亲身经历感觉到,文化改革要整体考虑,这支队伍怎样有序地合理地科学地改革,对戏曲要有收有放,收要收的合理,放要放的和谐。要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一个阶段,市场萎缩的很厉害。尤其是北路梆子,区域性小,院团少,从艺人员也少,市场很不好,我们这个剧种很脆弱,市场不大,受众面不广,简单地推向市场,不利于艺术事业的发展。
笔者:北路梆子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政府为了很好地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成立北路梆子剧院,财政全额负担,现在情况怎么样?
杨仲义:忻州两个团合并了,原来的人头费要有所增加,但现在还没有实施。合并的时候领导的想法是不错的,特别是北路梆子是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团支撑着一个剧种,不容易啊。有一个团完了,力量就等于削弱了一大部分,载体就小,所以应该好好保护。以前剧团是差额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将近50%。这50%是这么计算的,不连地区补贴工资,不连绩效工资,把这两部分去掉的50%,我们三级演员大概600左右,二级演员800左右,我一级六档,现在1400多元,演职员们的整体收入确实太少了。怎样使我们的生活好一些,物质条件好一些,我们从事精神层面的这一部分人让他精神更充实一些,精神和物质的结合更平衡一点,更和谐一点,更科学一点,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发展了。
我们戏曲要大发展大繁荣,但我们离大发展大繁荣的距离有多大?我觉得非常大。山西有多少个院团?有多少台好戏?当然好戏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所谓观赏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我们没有多少,实实在在说我们是浪费国家的钱。尤其是一些大剧目,好多是在玩着繁荣和发展,我是这么理解的。但这种繁荣,老百姓又能真正得到多少实惠,能不能看到,看了几次,看了这场戏又能受到多少教育和精神上的满足?不见得,真正的脊梁是还戏于民,戏剧的脊梁是在基层剧团,戏曲的观众是广大的老百姓、广大基层群众。但是,我们这一块却恰恰是,县剧团全部垮了,基本没有了,忻州原来有14个剧团,现在都没了,个别县剧团也成私人的了。
政府买单百姓看戏,还有长治的“文化低保”,这种做法我认为很好。戏曲的根在民间,但老百姓还是弱势群体,没有多余的钱买票看戏,国民经济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让老百姓得实惠,排出好戏来要多演,让老百姓能看到。这样我们的事业就发展了,剧目也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满足,文化也得到了繁荣,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笔者:很多“梅花奖”演员都担任剧团的团长,对于个人和事业来说利弊体现在哪里?
杨仲义:我觉得,如果是剧种标志性的演员,为了给他搭建一个平台,为了展示他的艺术,当团长是最佳选择。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但在管理上很有能力,那也可以去当团长。“梅花奖”首先是说他在艺术上是突出的,是有影响的,是品牌。市场经济相信品牌的力量,有品牌就能闯市场。但是像我,我真不想当团长。为什么?我这张品牌不足以养活一个剧团,可能我这个品牌一年能赚一百万,但是需要吃饭的一年最少要二百万。换言之就是说,让那些能够养活了一批人的人去当团长,让那些有能力把剧团办得很好的人继续当。像我这样不具备的,还是下来的好。
笔者:假如您不当团长了,准备干什么?
杨仲义:我是北路梆子传承人,我希望能培养接班人。我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在省里得过一等奖的青年演员,一个是得过小梅花奖的。他们愿意跟我学,愿意拜在我的名下,但我一直没有明确收他们一来,我不愿意过早收徒弟,因为我也在发展,二来我还在观察,尤其是对他们品德的观察。观察好了,才能定下来,定下来后就要教育他们为这个事业去奉献。既然是我的学生,我就要对他的各方面严格要求,不滥收不图多。我现在这年龄也能给他们言传身教,我是怎么演的,既能给他们说出来也能给他们示范出来,这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我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学习的几年中,收获很大,我自己认为我能当个好老师。现在北路梆子后继无人,这是最要命的事。
如果我不干团长了,我会把我的精力的一半用在演戏上,另一半用在培养下一代身上。我还想办个学校,然后办个民营剧团,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这个路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