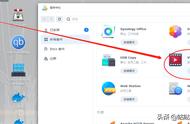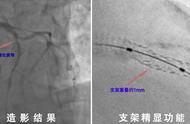合谋
Metro公司的墙上,贴着200个女模和180个男模的照片。恐慌和凝视不会阻止更多的新人进入这个行业,金字塔尖上的成功范例像强大的磁石吸引着众人趋之若鹜,却只有极少数模特的身体价值得到了肯定。繁荣的假象掩盖了底层的尴尬境遇,名模吉赛尔·邦辰净收入达1.5亿美元,但是大多数时装模特的平均收入只够付纽约的房租。
米尔斯认为,对一个模特的定价来自于行业内部的合谋。外形和美丽在时尚业分道扬镳,好的外形未必是大众眼里的「美丽」,外形标准的裁定权掌握在媒体和商业圈的少数人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批量生产的成品衣服替代了高级定制的时装,衣服有了固定的尺码和标准规格。模特的身形必须也像成衣一样被量化生产,贴合合适的尺码。设计师偏爱苗条的模特,0到4码是他们的最优选择,0码模特大概是7岁少女的身材。
生产者们表示无辜:「我不想让所有人看起来瘦弱憔悴或者就像他们真的要死了一样。但你知道一条崇尚完美的裙子穿在12码的人身上,绝对不可能比穿在8码的人身上好看。」
经纪公司、设计师之间互相模仿,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审美品位,使外形的审美标准不断畸变。这种关系和友谊是时尚业的根基,它通过模特这种介质进一步影响着大众的审美。
「模特的『外形』是社会不平等的视觉体现……外形是权力表现的象征,是性别、种族、性取向和阶层的交接点,是我们想象中的社会差异和幻想的视觉表现。」米尔斯运用了女性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的观点来解答这些现象。史密斯认为,理想的女性美是不断追求生产的资本主义机器中难以剥离的一部分:「总有工作要完成。」
时尚行业总是在扩大高端时尚与大众审美的差距,鞭策女性她们永远有「进步」的空间,从而实现资本利益的转化,对女性身体进行物化。女性不断向虚无的目标追逐,时尚业不断获利。
重压之下并不全是沉默。
2007年2月的一个下午,伦敦时装周的第一天,早春的冷空气还没有散去,人们还穿着单薄的棉衣。一群人聚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前的克伦威尔大街上,两点刚过,她们纷纷按原定计划举起系在脖子上的牌子,有几行不同的黑色的大字:「我们要时尚,我们也要身体的多样性」,「从什么时候开始,时尚业有了对身体的仇恨?」
这一场运动的幕后运作者是伦敦当地的女性组织Any-body.org,由女权活跃分子苏茜·奥巴赫创立。抗议的目标是伦敦时装周依然沿用「骨模」,对女性的身体多样性构成的威胁。
召集公告里,Any-body.org列举了参加抗议活动的理由:「如果你曾经进过试衣间却发现没有任何合适的衣服;如果你在看完时尚杂志后,觉得自己丑陋;如果你有个女儿,你希望她将来能爱自己的身体。」那场活动最后召集了数百个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女性。
2007年的那次抗议催生了一批类似Any-body.org的社会组织和全球范围的身体平权运动,她们在全球各地开设讲座,围绕着「身体多样性和社会控制」演讲,批评的对象常常是那个「万恶」的时尚业。
2014年,一则广告让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陷入舆论危机。广告展示了8个超模的形象,打上了「The Perfect Body」的字样。超过15000人签署了申诉书要求道歉并停止这则广告的传播,#iamperfect专题在推特上应运而生。
多年的抗议运动让T台上渐渐地出现了有色人种,大码模特。2018年,美国的大码模特特苔丝·霍利迪穿着翡翠色的丝绸泳衣,登上了《COSMO》杂志英国版的封面。
米尔斯对这些变化存疑——那只是在维持表面上的平等,更像是时尚行业为了招揽消费者而做出的妥协。「这些模特主要在照片拍摄和走秀中被用来诠释『异域』主题,选择他们只是为了增加『对于当时流行思想的额外颤动』。」
FashionSpot在今年3月对2019年秋季全球模特预订情况做了调查,发现大码模特比例不到1%,还有下跌的趋势,非白人的模特只有38%左右,不到总数的一半。

维秘模特在后台
偏见
田野调查三年后,金融危机的来袭击垮了多家模特公司。米尔斯突然被告知Metro公司将关停业务,经纪人用150美元把她打发走了。脱离模特身份后,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将她的田野所得写成了《美丽的标价》一书,它同时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她得以在纽约大学顺利毕业。
2011年,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却没有获得时尚界的同等关注,米尔斯可以理解其中的差异,这本书所描写的现象在时尚行业里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人会在乎它」。
她发现,即使离开了模特行业,女性被凝视和受偏见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米尔斯在面试波士顿大学的助理教授时,故意戴了框架眼镜,穿着沉闷的职业套装,她认为自己需要通过顺应某种社会潜意识来获得工作,「如果女性在工作中表现得优秀,她一定不好看。如果女性打扮得太过好看,那她的工作一定干得不怎么样。」
平时在学校她几乎不化妆,着装会选择松垮的职业便裤搭配灰色的羊毛衫。只有在周末,她才会打扮自己。
但这样仍然不够。在波士顿大学任教后,米尔斯时不时会听到同事们对她的研究的议论——她做过模特,写过时尚和女性文章,她的研究一定不够深刻和严肃。为了不被贴上轻浮、过于女性化的标签,米尔斯只好小心地为自己定位:她不是研究时尚和时尚模特的人,她是研究文化产业及其衍生产品的人。
某个导师评价系统对米尔斯的评价是这样的:「她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优秀教授,她可以用她的智慧和像模特一样的美貌让你对这门课感兴趣。」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她的名字,总是跟着一个标签——「全世界最美的社会学学者」。
偶然的机会下,米尔斯路过了曾经工作过的Scene公司,公司里的海报墙和杂志架子都空了,只剩下几个座椅。贴着模特卡片的塑料板已经被撤下,留出一块白色的空间。仅留下几位经纪人在为公司的业务收尾,近三十年的Scene走向了末路。公司的创始人海伦告诉米尔斯,她接下来会去为电视节目试镜工作,从事创意行业。「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时尚是如此的无关紧要。」
闲聊过后,米尔斯走出了Scene公司所在的大楼,回头望见大楼的黑色玻璃窗上贴着许「出租」的标志。踏在坚硬的东伦敦人行道上,她感到自由。
如今,米尔斯和一位大学教授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生活平静。
「我现在快40岁了,女性在开始失去美貌的时候就会意识到美的力量有多大。」米尔斯后来在接受访问时说,「美貌会失去,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我现在想到最好的方法是,关注其他让我感到有力量和自豪的事——我的事业、家庭、内在幸福。」
她有时会回忆起多年前,公司的经纪人坐在桌前,微笑着向她解释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这里,我们不能给你星星和月亮,但是我们能尽力为你提供到达那里的途径。」
他为她描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就像他对所有模特说的一样。


阿什利·米尔斯
参考资料:
1.《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阿什利·米尔斯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阿什莉·米尔斯 | 从T台到讲台》,时尚COSMO杂志;
3.《前模特出书称这一行低收入更普遍,成片上万的失败者被掩盖了》,第一财经;
4.部分数据引自FashionSpot2019年3月调查报告;
5.The Boston Globe:A Former Model Delves into the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