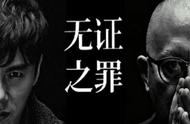《窍哥》 (1993)
年轻时担主角,与好导演和德高望重的演员一同工作,出好作品,宁理几乎摸到过天花板了。到28岁,春风得意之时又觉察到一种年龄危机——即便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宁理都觉得自己老了,小学毕业时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了五分钱一场的电影,而得花一毛五了,他很快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变成老人然后死去,像电影《平鹰坟》里一样的,挖出一个骷髅。他在被窝里痛哭一场——必须做些什么。
像是要替孔维本完成未竟心愿一样,1996年,宁理去了美国。
结果呢,只是从一个泥潭踏进另一个泥潭。他讲过很多遍刚出国时的窘境,因为缺钱而买最便宜的罐头,加点水兑成汤,去二手店买五块钱的牛仔裤十块钱的毛衣,去送报纸,当房屋中介等等。在终于有机会成为邮局正式员工、进入稳定体系前夕,他忽然敲了自己几下:我到美国干什么来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答案是,还是喜欢演戏。
“突然觉得我人生就这么长,从小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这个做那个,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那就任性一把吧。”宁理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念电影制作研究生,“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还得要打工,还得要生活,拍东西得自己掏钱买胶片。这东西不但没带来收入,还会让我在经济上透支,唯一支撑我的就是对它的喜爱。自己喜欢,能咋办。就像谈恋爱似的,中午休息时间才20分钟,头天晚上工作还没睡好,但是男朋友说咱一块吃个饭,咱一块到哪儿见个面,感觉跟打了鸡血似的,就是得去。喜欢嘛,没办法。”
明尼苏达州的寒冷是出了名的,有一段时间宁理要早晨6点多从住所出发,步行去剪辑室,走20分钟。后来《无证之罪》在哈尔滨拍摄,从12月到来年2月,室外的温度十分钟就能把人冻透,嘎吱作响的冰雪使他想起明尼苏达常走的那条路,想起那时候略矫情的自我感动,觉得“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寒冷从此变成一种记忆,打着哆嗦,感到兴奋,肾上腺素飙升。
《阙里人家》中爷爷孔令谭早对孔维本说过:真正有志气的人不走捷径。当然啦这样的生活很艰难,需要一点真正的勇气。
过了很多年一回头,宁理意识到焦虑的30岁简直年轻得不得了,并领会到人生是一个经历和体验的过程,“都是要一个人自己走过去的”。

《阙里人家》 (1992)
如父如子
宁理说,真正让他成熟起来的是成为父亲。
小时候父亲常常出差,宁理想象他是特务,丝丝拉拉玩着他的半导体,出差前答应带他去哪里玩,回来后忘得一干二净,一定有人冒充了他。不过比起对孩子们严厉的母亲,父亲更温和。新出版的《三毛流浪记》小人书要好几毛钱,他犹豫着不敢跟母亲讲,父亲则说那是好东西,给了支持。
宁理11岁的时候,母亲因车祸意外离世。那是礼拜三的下午,他和姐姐、弟弟一起在下象棋,“这个象棋很特别,是手工做的。”接受《人物》杂志访谈时他曾回忆,“那时候的家庭普遍比较拮据,买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笔开销。我妈妈是医生,她就自己画了个棋盘,用医院输液瓶上的橡皮塞当棋子,然后请会书法的人在上面写上车、马、象、士、帅。玩着玩着,突然一个堂姐来了,说我妈妈被车撞了,去世了。当时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个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还想那她晚上还能回来给我们做饭吗?后来每天每天,逐渐逐渐,意识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
父亲买了一台手摇留声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后来音乐在宁理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喜欢甲壳虫乐队,喜欢“The love you take equals the love you make(你付出多少爱,便得到多少爱)”这句歌词,他把人物表演视作一场交响乐,或者说人生就是交响乐,“它有时候是快的,有时候是慢的,任何能给人带来美的东西都是有节奏的。”
不过原先温和的父亲开始变得严厉,他调皮,有时候就被打骂。
后来宁理问过父亲,为什么他变得那么苛刻。父亲说,爷爷很早去世,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席,因此他特别担心自己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失职的父亲。
20年前,宁理也成为父亲。大女儿出生那天宁理在产房看到她,“我真的特别吃惊——怎么刚出生的孩子那么难看,皱皱巴巴的像青蛙一样,绿不拉几,当时我想这孩子正常吗?我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女儿出生了,他说太好了,孩子漂亮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书上说的什么一道光什么巨大的神圣都没有,你只能说看到一个孩子皱皱巴巴的。”
“可是慢慢地,当她真的能看着你的时候,当她的小手能攥你的手指的时候,那一瞬间,你突然就觉得,我的天,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他保留着一页女儿的作业本,上面是女儿写了两行的日记。当时他以为女儿敷衍了事而大为生气,一把撕掉,女儿愣愣地看着他,“没有哭,完全没有哭,但是那种没有哭比哭更扎心,所以那张纸我偷偷把它粘起来,一直保存着,提醒我自己,一颗心灵和另一颗心灵可以讲道理,但不能伤害它。”
宁理想起小时候有一天半夜醒来,全家人都住在一间屋子里,他看到父亲在灯下一边给他缝书包一边落泪。他好像终于开始理解父亲了,粗糙的,矛盾的,小心翼翼的。
父亲对他的影响极深,如何在人生略有错位时也要认真过活、努力发现乐趣、不要抱怨、对人事物始终保持包容和理解,都是从父亲身上学到的。
“父亲”也因此折射在了他的许多角色上:出演《无主之城》时他拿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跟剧组说,一个退休的略带些古板的老教师该穿成这样吧;《警察荣誉》里陈新城出差前反复叮嘱女儿一个人在家时关好门窗、煤气,那是他在生活中也常和孩子们交代的;哪怕是《无证之罪》里如此漠视生命的李丰田,*死法医的妻子和女儿,也是因为法医间接导致了他从未谋面的儿子的死亡,是父亲的复仇。
如果宁理要自己创作一个故事,他想他也愿意写写亲情。

《爱情神话》 (2021)
影视是一颗糖衣炮弹
如果细看宁理出演的每一个角色,会发现他热衷现实主义,契诃夫式的毫发毕现和暗潮涌动,也热衷在表演中对人性深入挖掘——
以三个间谍为主角展开的《对手》借谍战外壳,讨论人至中年的困境,宁理是其中最冷血的林彧,为了工作切割掉所有生活,他知道自己饰演着“反派”,也饰演着普通人,会在工作与生活产生矛盾时陷入巨大的迷茫和悲哀;

《对手》 (2021)
《无主之城》中的退休教师刘正毅总是拿着一本《蝇王》,这是宁理为角色的内心信仰和悲剧精神所做的设计,戈尔丁笔下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治理的民主派,强烈地暗示着刘正毅对人本身的失望;
《沉默的真相》中法学教授、刑辩律师张超为完成学生遗愿,终于从沉默走向冒险,宁理觉得他们悲壮,在官商勾结的势力迫害下,翻案如同蚍蜉撼大树,在剧组他无意中又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忽然泪如雨下,于是借角色之口表达对他们的礼赞:“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或死神夸口你在他的影里漂泊,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只要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