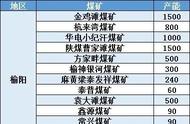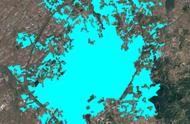1933年,陈独秀在朋友包惠僧的介绍下,曾给当时《中央日报》的社长程沧波写过一个声明。声明上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这份个声明最后并没有被发表,但鉴于陈独秀和程沧波的关系,他愿意将这个声明交给与自己曾有过龃龉的人,表明他对自己“托派”的身份是多么介意,甚至成为了他一个不小的心结。
“托派”,这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充满了“敌意”的名词,来自与中国同属于一个阵营的苏联。1926年,季诺维也夫就直言不讳地说:“同志们,这应当理解为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言语中的“争权夺利”指的就是列宁去世后,出现在苏共中央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纷争。
两人的斗争不仅体现在对苏联政治的争夺,还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国共两党达成党内联合是斯大林所支持的,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倒退,主张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中山舰事件”之后,受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导致了中共受到很大的损失,斯大林的权威受到了质疑。

1927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对斯大林心怀不满的群众和中国留学生们突然打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和口号,并与当局发生冲突。
“红场事件”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震惊。不久,参与游行的中国留学生被一一遣送回国。临行前,托洛茨基秘密向几个人交代了回国的任务,甚至允许他们脱离中共单独成立自己的组织。
这些人回国后,因为遭受蒋介石迫害的中共人员损失严重,他们便直接进入高层,得以担任重要职位,为之后成立“托派”组织造成了人员上的便利。
1928年12月,这批人中的几个以梁干乔为首,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叫“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梁干乔为该组织起草了政治纲领,还被委派为华南方面的负责人。他们的中央机构叫“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1929年4月,他们创办了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1929年9月,被“我们的话派”拒绝的陈独秀因在党内受到否认,又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怂恿,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做派反对派”,并于1930年创办机关报《无产者》,成为第二个托派组织。
1930年1月,和梁干乔一起从苏联回国的刘仁静因之前与托洛茨基有过交谈,自诩为“老托派,并于从“我们的话派”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人成立了新的中国的第三个托派组织——“十月社”。
同年,赵济等人也成立了中国第四个“托派”组织——“战斗社”。
1929年底,刘仁静曾写信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于是,刘仁静穿梭于几个“托派”之间。终于在1931年5月,由陈独秀号召,几个“托派”组织召开了统一大会,陈独秀任中央*。
但因为组织成员动机未纯,信仰不坚以及托洛茨基理论本身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因此仓促统一起来的“托派”再次陷入分裂,甚至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发生了马玉夫和谢少珊叛变事件,几乎将整个“托派”的中央常委一锅端,连陈独秀也被判以”危害民国罪“入狱。
之后,”托派“树倒猢狲散”,其他成员变节的变节,被捕的被捕,投降的投降。不过几年时间,“托派”在中国就成为没什么影响的小团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