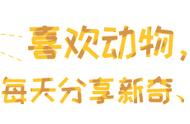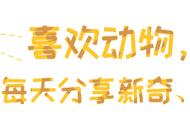布里斯班动物园里的澳洲野狗。很多中国游客看了都嘲笑——这土澳真没见过世面,竟然把中华田园犬养动物园里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白人陆续大规模殖民澳大利亚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这种奇怪的“野狗”。
白人们圈养的牲畜,时不时的,就成了野狗们的盘中餐,尤其是它们对绵羊的“破坏力”,要远超过其他食肉动物。
另外,和狼不同的是,澳洲大黄们虽然名字里带着个“野”字,但它总归还是狗。

一只眼神忧郁的长腿澳洲大黄
早前,纯食肉型动物的狼在被人类驯化成狗的过程中,获得了淀粉消化能力,逐渐进化成了杂食性动物~这也构成了狗和人类共同生活的生物学基础——毕竟,能吃到一起,才能过到一块。
所以,野狗跟人类一样,都属于杂食性动物,人吃的,它都吃——这样一来,相对于和人类有着明显“距离感”的其他野生动物,澳洲野狗更愿意接近人类的定居点,去翻找那些人类丢弃的厨余垃圾,“顺便”开开荤,“品尝”一下人类们养殖的各色肥美的牲畜。
几个世纪以来,野狗给澳大利亚的农场主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历来,澳大利亚农民总会定期组团捕*野狗,来人为的限制“澳洲大黄”们的数量,以维持生态平衡。

偷鸡的澳洲大黄
在肉体上“予以消灭”的同时,他们还想尽了办法,来屏蔽这些“不速之客”。
比如,全世界最长的建造物之一就是设在东南澳大利亚的一道跨度超过8000公里的防护栏。它打造于20世纪20年代,用来隔离澳洲野狗,以保护农场的动物。
同时,有些农民们也会选择搞些“心理震慑”,比如把那些被捕*的野狗挂在村口,以警告后续准备进犯村庄的“澳洲大黄”....

这时候,西方的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去哪儿了?
当然,除了隔离和消灭外,也不乏有一些野生大黄自小被人类收养,成了真正的乖巧的“大黄”。
有实验证明,如果从把澳洲野狗从小狗崽起就进行人工饲养,长大后,它们和普通狗子的表现并没太大区别(除了个别时候,攻击*比普通狗稍稍强了一点),并不需要专门的驯化——只要你按时投食,摸摸毛。
比如,对于人类的指令和手势,他们是有明确反应的,能够体现出较好的服从性,而不像狼那样,对人类的比划和吆喝,毫无感觉,完全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