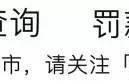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为贝聿铭)
怀着有朝一日盖出自己的国际饭店的梦想,18岁的贝聿铭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邮船,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不过他对当时过于传统保守的宾大建筑系颇为失望,仅仅两周之后又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师从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教授。
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正是中国最为风雨飘摇的时候。也正因为这样一个转折,贝聿铭经历了他同时代其他西方建筑师所不曾有过的“生命体验”。

贝聿铭年少时与家人的合影。
提及那段童年经历,贝聿铭仍会感慨万分:“那时对于新世界的强烈期待掩盖了一切悲伤,对于未来的冒险,我无限向往并充满好奇。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有机会去目睹一个新世界。”
这个关于建筑的新世界,也成为了世界的一个新视觉。
多年后,在一个访问中,贝聿铭说道:“有人问我中国对我的影响,是有的,有些人到了美国大大改变,有些人则一成不变,我则是在中间,有些改变,但是我以中国为根,长出西方的枝叶。”
事实也如此,贝聿铭的心从未离开过中国。

贝聿铭。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就是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被迫将银行搬到了重庆。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为了谋生,贝聿铭开始在波士顿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做了各种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这也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作为建筑师的一种营养资源。
1942年春天,在与相恋了4个年头的陆书华(英文名叫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译成“卢爱玲”)毕业后第五天,他们就举行了结婚典礼。之后,在普林斯顿时,贝聿铭与陆书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字颇有意味地取为“定中”。

贝聿铭与太太的结婚照。
1945年初,贝聿铭和太太回到剑桥,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木质唱片架,打算用来存放将来有一天能带回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身边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
为了向导师格罗皮乌斯证明“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贝聿铭拿出了他的作品——他设计的一座两层楼的上海艺术博物馆,上面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西方艺术的公开性很强,建筑要与之相匹配;但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是一种偏私人、隐秘的欣赏活动,所以建筑风格也必须有别于西式博物馆。”贝聿明解释说。
格罗皮乌斯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在向一本建筑杂志所写的推荐语里,他写道:“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很好地坚持基本的传统特征——即,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却不会放弃设计方面的进步观念。”
这句话,几乎创见性地预言了贝聿铭一生的建筑事业的特性。
1946年,贝聿铭从哈佛毕业,受格罗皮乌斯之邀留下来任助教,彼时的贝聿铭还在等待着回中国的时机。“如果有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届时就很难脱身。”1946年出生的贝建中说,“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特别教几个孩子中文的原因”“他们总想着以后早晚要回到中国。”
然而,眼看着中国又陷入一场内战,贝祖诒再一次写信劝阻了儿子,等到贝聿铭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是1974年。
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雄心和悠久的美
令人动容的是,1982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贝聿铭,重回少年成长地中国香港,为了向父亲所做的光辉业绩致敬,贝聿铭接下了设计中银大厦的业务。
香港似乎是可以让贝聿铭得心应手开展业务的地方。香港与贝聿铭本人一样,把新与旧、东方与西方合为一体。香港是海外华人网络的枢纽,也是在文化和地理上通向祖国的大门。
“我属于那种把几何性作为设计动力的建筑师,我们必须在几何学的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变化和组合,这还不是全部,还有空间、光线等很多因素。如果没有光线,就没有所谓的形体。太阳光具有神奇的魔力,因为它的变化是如此丰富。”贝聿铭对于建筑几何学的理解,通过香港中银大厦得到了最为生动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