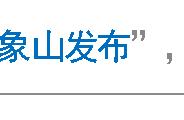(七十年代染织厂的女职工)
现在人们的衣裳啊,可真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林林总总,琳琅滿目。各色各样的cloth(布匹)把人世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老头象小伙,大娘象姑娘,帅哥象潘安,小女象花朵!
也是的,中国进步真快!改革开放也有四十余年了。那以前,整个华夏大地,人们穿的衣裳基本上是黑、灰、白三种,即使多一色,那也是军服草绿色,一般老百姓是望尘莫及的!
我高中毕业留城以后,先在市蛋品站做临时工。做到第三个月时,突然接到街道通知,要我去拿“报到证”到市染织厂上班。
我一看四四方方的报到证很高兴,因为“报到”二字后面还注一括弧——(三性工)。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
什么是“三性工”呢?我先疑惑以为是留城知青招工啦?喜得我逢人便说,哪晓得?有人吞吞缩缩地告诉我:“三性工”,就是“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还是临时的!我两耳一耷,怎么还是姓“临”啊?
在报到的那天,染织厂工劳科胡科长对我们一大帮子留城知青老姿老味地“训戒”:
“染织厂是国营大厂,是要招工的!你们好好干!干好了,‘三性工′可以转为正式工!”
我听了很激动,决心好好干!争取转正!
我分在染布车间,从染布车间厂内往北走三、四十米便是染织厂大门,大门临德宽路,与德一小隔路相望。

(此处是原安庆染织厂大门旧址。现在门口挂了许多招牌,但还是染织之内的老本行。)
染织厂主要是“染”,所以染布车间举足轻重!市里也很重视,一下子给这个厂分来几十个留城的高中生当“三性工”。
染布车间有几百个平方,隔成了几大间,分别安排“打布”、“炼布”、“染布”、“烘布”、“验布”等工序。
我被安排“炼布”,值守“高压炼布锅”。
何谓“高压炼布锅”?
那就是通过高压煮炼的方式,除去黏附在纤维织布上的天然杂质。
说通俗一点就是将“生布”变成“熟布”。
“高压炼布锅”有三米来高,三、四吨重,象一头大象窝在染布车间的西南角。

(网络截图。当年的“高压炼布锅”比它还要高大,四周有围子,有铁梯,上面还有一个大平台。)
锅上有一平台,平台一侧有一铁梯,工作人员上班时顺铁梯登上平台,接过运转机输送“打布”(又称“烧毛”,是用物理法除去布匹表面杂物)后来的“生布”徐徐落下锅内,一次煮一百二十米,分别注入浆料和煮炼剂,再用铁棍绞紧锅盖,最后启动高压阀煮练三个小时。
当时正值盛夏,外面骄阳似火,锅台犹如蒸笼,旁边有一台自制的大电扇,马达轰隆隆地响,扇叶刺喇喇地转,响得人耳发鸣,扇得人头发晕,再加上热热热,还必须得穿上工作服,讲一句脏话,那身上通体都在淋水!这种滋味真叫人难受!
有次我热得莫奈死活,还没等我倒下,只听见“染布”那儿一声惊呼:
“快来人啊!小苏昏倒啦!”
“染布工”苏传年热得中暑休克,倒在了染锅台旁,幸亏抢救及时……
“高压炼布锅”热,实际上“染布”除了热,还要闻那刺鼻的染料剂味,那时也没多少环保慨念,大不了通过苏传年“休克”事件后,多配了几副口罩。
但也有让人喘口气的时候,那就是停电!
偌大的染布车间一停电,“刷!”的一下子静了!尤其是上夜班,更是漆黑一片。
大家纷纷避开组长,绕掉工段长,自找拐拐落落角根儿,一躺下,一闭眼,快快活活地眯上一小会!
在这个时候,我这个“高压炼布锅”就成了香饽饽了。江顺悄悄地登梯,王崇志轻轻地猫腰,韦大忠、程金龙、马新麟、方平等间或上来,拽上一个大垛布匹包儿撂倒在地,人往上一爬,包上软软的,四周静静的,空间黑黑的,脑壳梦梦的。
尤其是“烘布工”张文耿和“打布工”程依婷来我这儿最勤。
张文耿等人来,我不怕,我就怕程宜婷上来,她长得小鸟依人,苗条清秀,尤其是那一对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深邃明亮。她一来,几个大小伙子睡不着了,我更不敢睡,因为这是我的“地盘”,要尽地主之谊。
我就陪她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直到电来了,灯亮了,机鸣了,人跑了,我也甩甩手站起身,装模作样地审视“高压炼布锅”上的气压表,超没超130度!
听说后来几年,程宜婷的母亲很喜欢方平,想招小伙子入贅,不知为何没成?但她俩以姐弟相称,这可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老了怕熬夜,但那时却喜欢熬夜上夜班,那是因为上夜班可以吃夜宵,还有那诱人的——肉片汤!
夜班十点进车间,捱到十二点,车间主任哨子一响,夜宵“驾”到!大家纷纷拿上自带的饭盒,跑向染布车间后门口。

(此处原是染布车间后门口旧址,出门口是德宽路街,街面仅宽三、四米。)
这个染布车间后门口直通德宽路大街,讲起来是大街,实际上只有三、四米宽。
一大帮子小青年站在狭窄的街面上,围上厨师,把碗一递,厨师神气地把毛巾往脸上一擦再往肩膀头上一搭,然后长勺一舀,每人一饭,一菜,一汤。
尤其是那一汤,是肉片汤啊!有大块橡皮大小,夹精夹肥的是肉,配上绿油油的青菜叶儿,上下浮动的豆腐片儿,若隐若现的碎葱花儿,飘飘乎乎的油星子儿,你领来了,自找方位,或站,或蹲,或坐,或倚,熳慢地喝,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慢幔地品……
在那个买肉要凭票,买米要搭山芋*年代里,能不花钱吃米饭,喝肉片汤,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醉了!
四十五年过去了,许多事已淡忘,但我始终忘不了染织厂夜班的夜宵和“肉片汤”!

(风华正茂十青年,共赴染布大车间,染来染去近半世,却染自己滿头白。
照片 左起
前排:苏传年、基建生、汪崇旺
中排:程金龙、王崇志、江顺、韦大忠
后排:方平、张文耿、马新麟)
盛夏。
凉秋。
初冬。
很快到了那一年的十一月份,留城学生正式招工,染织厂那一批所谓的“三性工”交上工作服(厂部强行收回),大家各奔东西……
别了——染织厂!
别了——三性工!
老实说,在染织厂上班近半年,三班倒,没有假,每天工资1.2元,算算也领了一百多元的血汗钱!是苦?是甜?——呵呵!
九十年代末,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一次饭桌上,我碰到了当年染织厂工劳科的胡科长,他下巴有一个黑痣,我一眼就认出他了,乘酒兴戏谑他:
“胡科长,我的′三性工′什么时候也该转正了吧?”
他大慨喝得更多,筷子一撂,眼珠子一翻:
“你……你……你是谁?我……我……我都下岗了!”

(行云流水写于202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