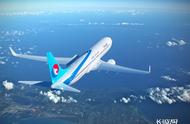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候鸟”棉痴赵国忠》的报道。
71岁的棉花专家赵国忠又来到三亚南繁基地,开始他的“候鸟”工作。
1977年起,每年秋天从石家庄到三亚,来年春天从三亚回石家庄,他连续当了44年“候鸟”。当年的毛头小伙,现已两鬓斑白。

2021年3月25日,赵国忠在三亚南繁育种基地查看棉花长势。(受访者供图)
育种梦想
“一个中专生,也要努力拿出替代美国岱字棉的新品种来!”
在南繁基地,曾经或依然活跃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甜瓜大王”吴明珠、“玉米大王”李登海等专家的身影,赵国忠就是其中一员。南繁基地的重要作用就是育种“加代”,利用这里常年高温的热带气候,让种子多繁衍一代。
赵国忠常年在棉田里风吹日晒,皮肤黑黑的,头发稀稀落落的。国字脸,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总是眯着,一副憨厚的老农形象,对所有人都是客客气气的,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
1950年,赵国忠出生于河北赞皇县一个贫穷的农家。1973年,他从石家庄地区农业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石家庄地区农科所(现石家庄市农科院)工作。
当时的农科所一无设备二无资金,更无育种资源。大地渴求良种,工厂急需优质棉。
那个年代,燕赵大地虽盛产棉花,但没有自己的当家品种,由于品种退化,产量长期不稳定,平均亩产皮棉只有27公斤。并且纤维品质也不高,不符合纺织企业加工要求,严重制约我国棉花生产和棉纺工业的发展。
赵国忠被农科所当作“宝贝”,“一个中专生,也要努力拿出替代美国岱字棉的新品种来!”老所长的话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赵国忠点头答应,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赵国忠接过课题,便开始疯狂地学习棉花育种知识,几年间学完十几门大学有关课程。他还利用冬闲跑了大半个中国,求教老前辈和同行,收集到300多份棉花育种的基础材料,把它们种到试验田里。
他虽过着“一铺一盖一碗一筷”的极简生活,但自此有了“让所有人穿暖”的梦想。

2月28日,在三亚南繁育种基地的棉田里,赵国忠在查看棉花长势。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棉花为伴
从播种那一天起,他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管:耕、锄、浇、防虫,还要一株株地记录结铃、抗病性、抗逆性等项目
赵国忠一直记着这么一句话:“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他说,育种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多看精选,多中选优,优中选优,才能出新品种。‘多少事,从来急’,但不能着急,又不能从不急。”
赵国忠的棉花育种技术有两道最重要的工序,一是做杂交组合,二是做田间选择。做杂交组合的关键在于选择好亲本,使亲本间的优异性状能互相补充,以便通过杂交使之融合到一起,以期优异性状能遗传给后代。田间选择的关键在于确定好育种目标,并能在实际操作中看得准、选得中,以便在千千万万个杂交后代中选到理想的单株。这是育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
农家的孩子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赵国忠认准的事,就一心要把它干好。40亩试验田里栽种下16万株棉花,他每天蹲在地里观察、选择、挂牌、记录,从中选出最优单株,他竟在地里整整蹲了10天。试验基地南早现村位于河北省正定县,距离农科所15公里,他骑着自行车寒来暑往,每隔两年就要换一条崭新的自行车外胎,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他都在试验田里度过。
在棉花田间选择上,从播种那一天起,他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管:耕、锄、浇、防虫,还要一株株地记录结铃、抗病性、抗逆性等项目。七八月骄阳似火,既是棉花结铃关键时期,又是棉铃虫猖獗时刻,他守在田间地头,隔三岔五地背着喷雾器喷洒农药,身上湿漉漉地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
这样的过程历经三年,一个新品种就诞生了。1978年,他在试验新组合代号为“1724”的棉花品种。“这个新品种是我在试验田里从第17行到第24行中间获得的。”
“1724”的优秀骨干系被他选出来,他为此编号“78-114”,含义是“1978年的第114株棉花”。
然而,选出了优系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种,还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定型等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而河北每年只能种一季棉花,加快育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加代繁育。
他把目光瞄向了2370公里外的三亚。

2月28日,在三亚南繁育种基地的仓库里,赵国忠在检查棉花种子。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南繁“候鸟”
我的头发是“免理的”,衣服是“免洗的”,被子也是“免叠的”
刚开始当“候鸟”那些年,赵国忠每年都背着一个大蛇皮袋装种子。他从石家庄到三亚,转乘火车、汽车、渡轮,有时要走上十天半个月。他至今记得当年的乘车路线:先从石家庄坐火车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到湛江,再从湛江坐汽车到海安,在海安乘渡轮到海口,再从海口坐汽车到三亚,从三亚坐汽车到崖州南滨农场南繁基地。
赵国忠随身携带一杆小秤、一把木尺、一根扁担。这根扁担陪伴了他南繁岁月最初的10年,担肥担棉担种,全靠它。
“那时,把棉种运回石家庄可不容易啊。”1983年4月,他运送108包棉籽回石家庄。路上要翻越五指山,要横渡琼州海峡,要经公路、水路和铁路,要坐汽车、火车、渡轮。当时,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岖不平,还要经过8个陡坡加急转弯。一边是陡峭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他在车厢里拿一根棍子顶着棉包,为的是不让棉包压住自己,有好几次急转弯时险些被甩到车外。每个棉包重30公斤,到湛江火车站后,赵国忠先把棉种卸下来,一包包地过磅,再一包包地搬到站台上。搬完最后一包,他一下子瘫在站台上,感觉“眼前整个世界在转动”,他才想起2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
还有一次,他在广州中转等车时在广场睡着了,一个警察看他衣服又脏又破,人又黑又瘦,以为是一个“盲流”,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询问。他拿出工作证和人大代表证,警察先是惊讶,然后向他敬了个礼,并连声道歉。
赵国忠初到南滨农场时,租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居住地离试验田远,中午就在田里啃凉馒头就咸菜。当时经费紧张,没钱雇工,所有农活都是他自己干。同行“评价”赵国忠:“头发又长又乱,像个要饭的,衣服皱皱巴巴,像个烧炭的。”他却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我的头发是“免理的”,衣服是“免洗的”,被子也是“免叠的”。
他自小就怕蛇,而当时海南的毒蛇很多,他尝试多种办法还是防不胜防。绿色的竹叶青蛇盘在棉枝上,灰色的眼镜王蛇和土地一个颜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有一次,赵国忠一脚刚要落下,一条眼镜王蛇突然立起,吐着信子发出簌簌声,准备向“来犯者”发动进攻。赵国忠一转身,不足两米处又一条眼镜王蛇立在那里。幸亏那两条蛇对这个陌生人表示了“谅解”,他才躲过一劫。
后来,农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房间里有了电视。可他每天都是固定看一个台——农场台,他压根没想到还有别的台可选。
多年前一个除夕夜,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床上,听着远处的阵阵鞭炮声,遥想着几千里外的家人,他默默唱着那首最喜爱的《常回家看看》,泪水不知道啥时候已流到耳边。他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永远忘不了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女儿日记里的爸爸“是一个只爱棉花不亲女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