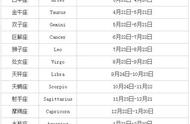甚至还有不了解的人打趣道:“也许中国人去到澳大利亚,光靠吃掉他们,就能把整个澳大利亚的兔灾解决。”
这种说法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的赞同,他们更好奇的是,为什么没人吃这些肥美的兔子?
一些人去问当地人,当地人只能一脸无奈地说:
“多年来,我们也不是没有吃过兔子,但是兔子的增长速度和我们吃的速度相比,实在是太快了。现在久而久之,很少有人对吃兔肉这件事产生兴趣。”

正如当地人所说,事情并不是单靠数量压制就能解决的,这种极端的生态环境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人类的傲慢。
而这一切,又要将时间线回拨到19世纪。
因为引入野兔,并不只是为了狩猎那么简单。

托马斯·奥斯汀,除了是一名平平无奇的英国绅士,还是驯化协会的会员。
所谓“驯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驯服,而是包含了物种迁移的意思在里面。
换言之,当时的欧洲盛行的一种思想认为,任何物种可以通过人为干涉,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成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托马斯当时,也是抱着类似的心态,将一些原本是欧洲的物种带到了澳大利亚。
以他为代表的驯化爱好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自然的轻慢。
曾有一个叫做弗兰克·巴克兰,在他的书中说过:“重新安排自然界的一切,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