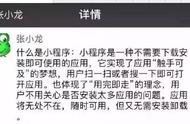上初中时,校园中心的坝子还是一片泥地,靠近围墙边长有一株洋槐,碗口粗细,歪着脖子,旁逸斜出,相比村里所见的那些洋槐,多了许多风情。这棵树以及树下的泥地,是附近班级男生女生的乐园。男生蹭蹭爬上去,又矫捷地跳下来,若有女生在场,男生们则卖弄得更为大胆夸张;女生喜欢在夏日午后,三五两个躲在清凉的树荫下说说心事,聊聊谁又和谁好了的八卦。
有年四月还是五月,洋槐花又开了,小学部唯一一个教音乐的男教师和他的家属一块儿来采槐花。在这所乡镇学校,男教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长得很城市,白白净净,头发微卷,一抹小胡子,举手投足间也是洋气的城市做派。
那时镇上有一家姓虞的,养有四个女儿,个个出挑:大姐最美,一股子天生的风流气韵;二姐知性,书卷气浓;三姐率性,有股男孩子的英气;老四年龄尚小,乖巧伶俐,是和我玩得蛮好的同班同学。
大姐读初中时便开始和这位教音乐的男教师谈恋爱,那时候真是惊动全镇,虞家父母也是极力反对。但几年后,虞家大美人还是嫁给了这个大她十来岁的男教师,出双入对,幸福得如糖似蜜。学生们经常见到男教师在教师宿舍弹吉他,虞美人姐姐就在一边伴唱,一双纤细白皙的手挽弄着自己柔顺的黑色长发。
真美啊,那情形。

男教师带着美丽的小娇妻,挎了竹篮子,来到洋槐树下。树并不很高,但要摘到枝头的槐花,却也不易。读初中的虞小妹早已小鸟般飞过去,要帮姐姐姐夫摘槐花。奈何几人都文雅秀气,摘不到那槐花。好在乡镇学校,找个竹竿是容易的,于是男教师就举着竹竿打槐花,虞小妹和虞美人姐姐在树下仰头接槐花,没接着掉地上的,就欢笑着拾起来放进竹篮。
一群学生目光欣羡,远远看着,仿佛那是一幅自己无法进入的图画。
这槐花拿来做什么呢?乡下孩子可不懂。我问虞小妹,虞小妹说,包饺子。
那个年代的西南乡村,面食无非面条抄手,饺子可是北方人的饮食,带着陌生的贵气。而且,还用洋槐花来做馅哪!真是让人无比向往羡慕呢。
男教师后来和虞美人生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男孩儿,卷发如父,滴溜溜的眼睛如母,但未及孩子读小学,虞美人便和男教师离了婚,不知去往了何处。

如今这些别人的故事,已过去有二十多年,这惊人的时光!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回想着这些褪色照片般的陈年旧事,洋槐花已在身后。
再过几日,这满树白玉般莹洁的花就该凋谢了,干枯在枝头,或者,纷纷扬扬于竹林间,地面上。那浓郁的甜香,也将在阳光里、在春风中渐渐淡去,直到消失。
可是它们毕竟曾经那么美好地盛开过,不是吗?
而且,明年,洋槐花还会如期盛开;只是,我们的青春与生命,都在老去,不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