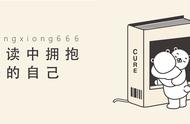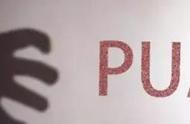在这种情况之下,教授PUA课程的机构也并不单纯,甚至有的如邪教一般疯狂。
导师们把自己塑造成无所不能的搭讪大师,洗脑男性。
让一些男性沉醉于内部同舟共济的兄弟情谊,误把导师们当成救世主或偶像一样崇拜。

还会给女性洗脑,强迫她们接受一男N女的模式。
一位导师就把成功搭讪过的女性全都聚在一起,以她们的「爸爸」自居。
享受其中女性为了争夺他而进行的争吵。
还让她们统一纹有他名字的纹身......
这样的PUA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畸形。
正像《警察荣誉》当中,警官在办案时一语中的:
他们把受害者物化的同时,也抛弃了自身的道德感。
仿佛对方只是一个任凭玩弄的物件,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PUA一词包含着许多痛苦、沉重的内容。
它的范畴也早已不局限于针对女性的围猎,更包括了亲密关系中不易察觉的情感操控。
从包丽自*事件,再到李靓蕾的小作文,PUA话题几度得到全网热议。
可现在,PUA也沦为又一个「互联网烂梗」,冲淡了它本有的公共议题价值。
曾经那些或愤怒,或悲哀的情绪,不再激涌。
玩梗带来短暂快感之后,剩下的是浸淫在奶头乐当中逐渐失去思考能力的麻木。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许多严肃的公众话语都面临相似的困境。
比如对家暴的玩梗。
刘洲成曾经多次家暴*的前妻,致其流产。
丑闻过去几年后,新女友直接官宣「我是新沙袋」,刘洲成则回以拳头表情包。
丝毫不以为耻,让人大跌眼镜。

评论区的网友也是配合。
纷纷用暴力抖机灵,彰显自己「幽默感」。
还有更刷新下限的「化粪池警告」。
杭州*妻案告破后,许多网友把凶手分尸、抛尸进化粪池的作案手段当成玩笑段子,制作成各种表情包。
一件残忍命案就这么被当成博眼球的工具。
让人不寒而栗。
同时,一些电影也遭到了类似的对待。
老片《贩母案考》中,女性被人按12元一斤的价钱卖给7个劳改犯。
原本是讽刺旧时代女性被物化的悲惨命运。
结果评论区却把它比成《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还有揪住女人的「卖价」作对比的。
当涉及到具体的当事人时,玩梗也造成了二次伤害。
在德普和安珀·赫德的离婚风波中,对赫德的恶搞就是如此。
大众把自己当作一个审判者,先入为主地断定她在作秀。
然后开启一场网络霸凌的狂欢。
模仿赫德的各种表情,嘲笑她哭得太假,咬定她在床上排泄……
仿佛关注的不是一场严肃的庭审,而是一场娱乐性质的真人秀。
同时,对赫德的恶搞也模糊了案件中关于家暴、诽谤等争议点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