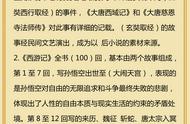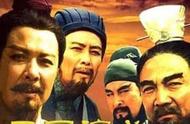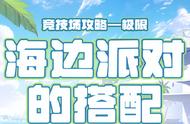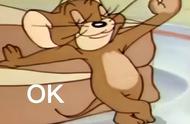造化神奇 依水而生
江苏多水,江苏的水形态各异,江苏的水有着独特的情韵,这是我对江苏省情特点最突出的一点认知。
在江苏工作期间,我常常讲起历经多地工作后的一个体会,就是对一个地方的域情,本地人或许是“身在此山中”的缘故,未必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很清晰的认知。外面来的人往往会于映照比较之中产生更加鲜明而敏锐的感触,反而能看得更加明了。
在中国,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运河皆备的省份只有江苏。这里辖江临海、扼淮控湖,京杭运河纵贯南北,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水面接近六分之一,平原面积占70%,水面和平原的占比在全国各省区中都是最高的,这里水网密布,有大小河流2900多条,大小湖泊290多个,五大淡水湖,江苏就占了两个,太湖和洪泽湖。
万里长江在江苏境内被赋予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扬子江。没有了金沙江的奔腾激越,没有了川江的险滩急流,也不像荆江九曲回肠,长江至此江面开阔、水静流深,浩浩汤汤与大海相会相融。就像人的一生,青春期总有些叛逆,血气方刚时不免躁动,待到阅历和历练多了,方才变得深沉含蓄、大度平和。

千里淮河虽然水量、长度未必居前,但却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古代“四渎”。淮河还与秦岭共同构成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广为人知。
说起淮河,那是一部交织着喜乐与哀愁、辉煌与苦难的历史。淮河流域平畴沃野,物产丰富,素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但宋至清近七百年的时间里黄河鸠占鹊巢、夺淮入海,直到1855年再次改道,把清清如许的淮河折腾成一条横贯苏北大地的废黄河。黄河改道给两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其裹挟的泥沙也重塑了苏北地貌,孕育了广袤的沿海滩涂。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治淮成效卓著,淮河两岸旧貌换新颜,呈现勃勃生机。江苏治淮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奋进的一个缩影。

“沧海桑田”的故事,让江苏来述说最为生动。
数千年来,大江大河大海的吐纳交汇,使这里成为泱泱中华最年轻的土地之一。唐宋之前,今天的南通还是海里的一些沙洲,经过千年“拼盘”,方有了今天的模样。盐城的滩涂资源十分丰富,现在仍以每年3万亩左右的速度继续生长,对人多地少的江苏来说,这真是一片神奇的“息壤”,是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当年北宋名臣范仲淹在盐城所修筑的海堤如今已成204国道线,而海岸线整整东移了50余公里。大自然的伟力,无疑是最雄奇的。
如果说,自然的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那么人工运河则是人类文明的杰作。江苏地势低平、水系发达,为运河的开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于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凿的胥河,有的说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时开凿的邗沟。近些年有人提出,更早之前的泰伯奔吴后,在今无锡梅里兴修水利开凿的泰伯渎,为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
无论是哪种说法,“运河之祖”都在江苏。

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和终点虽然都不在江苏,但1794公里的运河有将近一半在江苏。大运河的修筑对沟通南北、发展经济、稳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大运河开通之后,中国以淮为界、南北分裂的时间大大缩短,特别是元明清三朝,大运河俨然成为关系社稷安危、维护国家统一的生命线。
从历史角度客观地看,隋炀帝其实完成了一件大功业,唐朝诗人皮日休曾留下点评隋炀帝的千古名句——“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今年6月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大运河当之无愧地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反映出中国人民超常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有人发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北部横亘东西的长城与东部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仿佛是写在神州大地一个巨大的“人”字。这样的发现具有丰富的想象,寓意却不乏深刻。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人民创造的两项最伟大的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伟力。而江苏段大运河河道最长,文化遗存最多,保存状况最好,利用率最高,至今仍是繁忙的黄金水道,因而江苏也当然地承担起了牵头申遗的任务并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