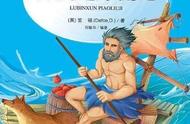鲁迅在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在45岁写的,追忆儿时快乐的时光。但据其弟周作人回忆,其实这个五彩纷呈的百草园是鲁迅先生虚构出来的,并非实有,或者说,他在回忆里加了滤镜和美颜。真实的百草园是这样的。
周作人《鲁迅的故居》:百草园名称虽雅,实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平常叫作后园。横阔与房屋相等,那是八间半,毛估当是十丈,直长不知道多少,总比横阔为多,大概可能有两亩以上的地面吧。
南头靠园门的一片是废地,东偏是一个方的大池,通称马桶池。园门右面是一座大的瓦屑堆,比人还要高,小孩称它为高山堆,堆上长着一株皂荚树,是结“圆肥皂”的,树干直径已有一尺多。园门左边靠门是垃圾堆,再往北放着四五只粪缸,存以浇菜或是卖给乡下人的。园的中间一段约占全部五分之三吧,那全是可以种植的土地,从中央一直线划开,种些黄瓜白菜萝卜之类。
园里的植物,据《朝华夕拾》上所说,是皂荚树,桑椹,菜花,何首乌和木莲藤,覆盆子。桑椹本是很普通的东西,但百草园里却是没有。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作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
何首乌和覆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这里的泥墙本来是可有可无的,弄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覆盆子的形状,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这句话形容得真像,它同洋莓那么整块的不同,长在绿叶白花中间,的确是又中吃又中看,俗名“各公各婆”,不晓得什么意思,字应当怎么写的。
百草园里的动物,我们根据《朝华夕拾》中所记的加以说明,大约可以分作三类。其一是蝉,蟋蟀与油蛉。其二是黄蜂,蜈蚣与斑蝥,还有赤练蛇。黄蜂本来只是伏在菜花上,但究竟要螫人的,也不会得叫。蜈蚣与斑蝥平时不会碰见,除非在捉蛐蛐,把断砖破瓦乱翻的时候,它们虽是毒虫,但色彩到底还好看。赤练蛇从来没见过,只是传说而已。其三是鸟类。《朝华夕拾》中说有叫天子即云雀从草间飞上天去,这个我没有见过。至于麻雀那自然多得很,鲁迅所记雪地里捕鸟,所得的是麻雀居多。
简言之,百草园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好玩。园中的废地,马桶池,瓦砾堆,粪缸,这是典型的大户人家并不鲜见的后园,毫无诗意可言。
可见鲁迅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发挥了丰富的想象,才在纸上构筑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儿童乐园,用充满童趣的笔法为现代文学留下一篇唯美的经典之作,被列入中学课本并且要求背诵,对几代人的汉语言审美影响极大。百草园也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隐秘空间和人间乐园的代名词,这个空间和乐园由植物的形象、色彩和味道构成。鲁迅的描写简洁,传神,准确,生机勃勃,令人向往。
那么鲁迅为啥要把本来并不存在的生活描述的如此诗情画意呢?因为在他苦痛的一生中,童年时期的幸福时光是唯二的亮色。鲁迅一生只有两段时光堪称幸福,一是家道败落前十年的“少爷时期”,一是和许广平蜗居上海的最后十年。中间三十多年,有的只是孤独,寂寞,彷徨,屈辱,流离,漂泊,挣扎,隐忍,颓唐,涉险......用他的话说,“吃尽了生活的苦”。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和许广平刚刚交往,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每天靠书信互诉衷肠。当时他在厦门大学教书,被同事排挤孤立,郁郁不得志,于是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取名《旧事重提》,后改名《朝花夕拾》。给许广平写信是憧憬未来的幸福,回忆童年时光是怀念儿时的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忆童年的时光,也都会把不快乐的事情抹掉,给回忆加上滤镜和美颜。毕竟比起成年的苦痛和伤感来,童年的那点不快乐真的不算什么。
鲁迅的文章,冷静,清醒,犀利,温厚。少年人读鲁迅,只觉有趣好玩;中年人读鲁迅,方知深邃高远;老年人读鲁迅,彻悟豁达通透。品读鲁迅,神交鲁迅,收藏鲁迅,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必备功课。每个中国人的书架上,都应该有一套《鲁迅全集》。
中国杰出的作家不少,但是鲁迅只有一个。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