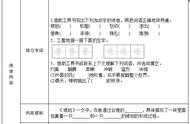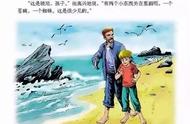“一带一路文明印记·阿富汗古代珍宝展”系列报道⑷
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中,蒂拉丘地遗址出土的一件狮形琥珀吊坠,引起了本次展览学术顾问、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赵德云的注意。
这件血红色的琥珀,被雕琢成一个蹲坐的小狮子,萌态十足,腰部还有十分明显的穿孔痕迹。这样的造型,在汉代比较常见,赵德云推测,这件文物极有可能产自中国,背后的文化交流意味不言而喻。
琥珀是松柏树脂形成的化石,颜色有淡黄色、褐色或红褐色,燃烧时有香气,可做装饰品。琥珀作为装饰品,出现的年代很早,距今3000多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曾出土一枚琥珀坠饰。从汉代开始,琥珀装饰品逐渐成为皇宫贵族的爱物,无论是赏赐皇亲国戚、后宫佳丽,还是皇帝御用的朝珠、文玩,都有琥珀的一席之地。

阿富汗大展上的狮形琥珀
狮形琥珀是辟邪形珠
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琥珀,来自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枚琥珀坠饰。
当年的发掘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高5.1厘米,略呈心形,上端残缺,中有穿孔贯通,应是一件坠饰。“两面阴刻纹饰,一面为蝉背纹,一面为蝉腹纹。”
这里说的蝉背纹,与金沙心形金箔和人面纹玉璋纹饰相同。
三星堆遗址距今有5000-3000年历史,这一件心形琥珀坠饰的出土,至少可以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在使用琥珀做装饰了。
在这次阿富汗珍宝展上,展出了一件来自“黄金之丘”蒂拉丘地5号墓的狮形琥珀。小狮子个头不大,长2.6厘米、宽2.2厘米、厚1厘米,蹲伏在地,身体中横穿一孔,与中国的辟邪形珠造型如出一辙。
这只蹲坐的小狮子,与1975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汉墓、现存于广西博物馆的西汉琥珀小狮坠,风格十分相似。

西汉琥珀小狮坠(广西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蒂拉丘地遗址的同一个墓地,还出土了带铭文的汉式连弧纹铜镜,让人不得不对这两件文物的由来展开丰富的联想。
关于墓葬的年代,发掘者推测在公元25-50年。我国学者根据墓地出土钱币及佛教艺术品的情况,认为其年代下限在一世纪末,也就是东汉时期。
赵德云在《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中,详细考证了琥珀的出土情况。
出土的琥珀珠饰,一般体形不大,长径不超过3厘米。从形制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圆形、半圆形、椭圆形等几何形制,也有少数呈不规则形;另一类制成动物形象以及壶形的琥珀最具特色,可能寓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其中的动物形象,除少数为猪、羊、鸟等外,像阿富汗大展上这种蹲踞的狮子形象居多,而且上有穿孔。
有的琥珀原本做工抽象,或出土时就已磨损不清,而两汉时期中国狮子艺术形象的“虎化”,在一些报告中或泛称为“兽”,或定名为虎,实际都应是狮子。
赵德云认为,这些制作成蹲踞狮子形象的珠子,应称为辟邪形珠,与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穿孔的狮形琥珀,御凶避恶的功能超越其装饰性。
西汉人史游撰写的识字课本《急就章》中记载:“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汉代人用一根绳子穿孔挂于臂上,认为可以除凶灾而卫其身。
鉴于当时辟邪形珠在中国十分流行,赵德云更倾向于认为,狮形琥珀和连弧纹铜镜一样,都是从汉地传来的。
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辟邪形珠的意匠(构思布局的意思)来自外来文化,然后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在小小的辟邪形珠上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和谐交融;另一方面,这些器物有可能辗转出境,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馈。

成都市区出土的明代琥珀串珠(成都博物馆藏)
古人称琥珀为“虎魄”
琥珀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这种美丽的化石,在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出现。
提起琥珀,不少读者会想起人教版语文教材中,德国作家柏吉尔的《琥珀》一文。当蜘蛛准备捕食苍蝇时,被一颗硕大的松脂包裹,最后,滚落在地的松脂球经过沧海桑田的沉淀,变成了一颗琥珀。
如果没有琥珀,恐龙迷可能看不到侏罗纪系列电影。如在《侏罗纪公园》开头,一位生物科学家从琥珀中提取了史前蚊子身体中的恐龙血液,利用DNA培育繁殖恐龙,还原了恐龙世界。
根据赵德云教授的研究,琥珀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得较早。西汉思想家陆贾的《新语·道基篇》中,就有“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的记载。在陆贾看来,琥珀与其他珍异同样是具有灵性之物。
不过,在汉晋时的其他文献中,琥珀多称为虎魄。
如《汉书》:“封牛……珠玑、珊瑚、虎魄、壁流离。”
《后汉书·西域传》中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珊瑚、虎魄、琉璃……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出“铜、钱、铅、锡、金、银、光珠、虎魄……”。
《华阳国志》说:“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人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玳瑁、虎魄、水晶……殊方奇玩,盈于市朝。”
《三国志》裴松之注《魏略·西戎传》,称为“虎珀”,较晚的《隋书》又称“兽魄”。
古人将琥珀称作“虎魄”,大概与民间“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的说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