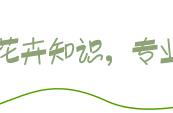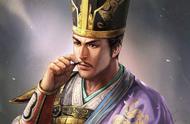“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中国人评价人品的重要尺度。
在著作言说里提到“君子”最多的人,当属孔子了。
孔夫子一生说的都是君子之道,所追求和倡导的也是道德完善、品行高尚的完美君子人格。
夫子之后,论必谈“君子”的当属苏轼。
苏轼的论说文里,几乎每篇都有“君子”字眼,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甚至有多个“君子”出现。
纵观苏轼的一生,都在追寻君子足迹,效法君子行为。
而他所谈论以及所坚持的君子人格,也长久地、深刻地影响了华夏千年的文人和文脉。

君子以正直立身
苏轼在《明君可与为忠言赋》说:
“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
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
然而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
在他看来,君子应该敢于直言不讳,正直不阿,心地坦荡,忠于国家,主动上谏,不顾个人利害甚至身家性命。
苏轼自己也如他的诗文所写,一生坦坦荡荡,率性天然,正直求真。
而他的这种道德上的内心剧本是他的母亲程氏夫人写就的。
早在东坡出生之前,程氏夫人就做了一件令全天下人刮目相看的事情。
当时,苏家在四川眉山城南纱觳行街上租住,兼作一些织品加工售卖的生意,贴补家用。
有一天,屋里的地面突然陷落,出现一个大坑。
里面露出一个大瓮,家里人惊喜地以为要发大财了。
但程夫人却平静地吩咐将坑洞填满,不取宿藏。
程夫人不贪恋来路不明的财物在成为家庭传奇后,对苏东坡的影响至深。
后来他身居高位时,廉洁奉公,不贪恋不义之财,即来源于此。
苏东坡十岁时,母亲和他亲子共读《后汉书》。
读到范滂传时,程氏夫人为范滂舍身取义,宁死也与宦官斗争的精神感动。
苏东坡见母亲动容,不由自主地说:
“孩儿我要是去做范滂,母亲可会同意?”
程氏夫人毫不犹豫地说:
“你要是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就是这句话塑造了苏东坡一生的道德标准。
后来,他被时代卷入变法之争。
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当政时,苏东坡觉得新法不利于民生,利用自己的影响极力反对,结果被王安石贬到地方去做官。
再后来,王安石下台,反对王安石的元老司马光当政。
司马光大力打击变法派,将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召回京城,准备重用。
苏东坡亲历地方治理后,觉得新法中有利于民生的部分,不应取消,结果又得罪了司马光,再次遭贬。
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傻帽”行为,却正折射了苏东坡“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正直品格。
如果他想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他和王安石、司马光的私人情谊,无论谁当政,都可以顺风顺水地坐享富贵。
但苏轼就是这样,装着“一肚子不合时宜”。
他明明知道反对皇上所支持的王安石变法,会遭到忌恨和打击迫害。
但仍不改其操守,并将重道、重节放在生命之上。
他在《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会有司根治札子》中说:
“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身成仁可*不可辱之语。”
正像他在文章中所说,他没有为了个人之功名、地位而改变自己刚正不阿、不肯俯仰随人的崇高品质。
“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正是苏轼君子人格的写照。
虽然他一生为党人倾轧、为小人诬陷,一贬再贬。
但他正直不屈,坦荡而不悔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光耀了千秋后世。


君子以豁达立德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写道: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二十一岁入京参加科举考试,在欧阳修的推崇下,名动京城。
三十四岁,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自请到地方任职。
四十三岁,因“乌台诗案”贬官至黄州任团练副使。
五年后回京,然后又到地方上任职。
五十七岁时又被贬官至惠州。
六十二岁再次贬官至海南儋洲,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
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横跨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永远是一个笑口常开的模样。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写这首诗时,这位曾经纵横京师的大才子,默默地在田间劳作。
生活上的艰辛暂且不论,心理上的落差也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意志了。
然而,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外放辟地也好,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
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
苏轼在《宝绘堂记》指出: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
君子要乐在豁达超脱,如果个人不依赖财富、名利、外物,快乐就到来了。
苏轼被贬黄州时,由太守变为罪人,等待他的是“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
廪禄既绝,衣食不给”,一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对此,他却能积极去面对,“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深谷”。
为改善生活,他在黄州城东一片田地里辛勤劳作,自号“东坡居士”。
自己打井、种菜、修建鱼池,还托人从老家捎来菜种,并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知笋香”,好象根本未曾受过打击。
在逆境中坚守自我、顽强不倒已是难能可贵,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乐观向上、热爱生活更是可惊可叹。
被贬儋州,他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当终于可以北归时,他欣喜,却也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被贬的日子虽苦,却无怨无悔,其中虽有倔强,但更多的却是豁达与坦然。
无关境遇如何,苏轼总是以一种空明澄净的禅悦之心来对待外部世界的一切矛盾和失意。
并将其化作一种恬然自适的心情,展现出君子最为宽广的胸怀。